《安妮特》剧情介绍
讲述一对好莱坞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安妮特的故事:丈夫亨利(亚当·德赖弗 Adam Driver 饰)是一位单口喜剧演员,妻子安则是一名歌剧明星(玛丽昂·歌迪亚 Marion Cotillard 饰),而他们神秘的女儿安妮特,又拥有怎样不同寻常的人生呢?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羽毛春天来了,春天菜鸟烘焙大赛第七季绝路桥风之王他的三个女儿人吓人南无阿弥陀佛!-莲台UTENA-薇拉我是一名教师WIXOSSDIVA(A)LIVE闯荡虎踞龙盘情人们小岛孔雀鱼风中的火焰1993空劫行动扑通扑通喜欢你外滩探秘第三季家政夫三田园4公主日记军医迷失:消失的女人我们要出海不法岳父母紫薇飘香龟岩许浚复仇少年无辜者
《安妮特》长篇影评
1 ) 囿于Adam Driver明星魅力的卡拉克斯
Driver在这部充满男性和父权暴怒的音乐剧中饰演了一个令人愤慨的喜剧演员。
他是这部影片的中心,可他的作用却出奇地模棱两可。
Richard Brody 文 原载于《New Yorker》 翻译 Rowena(有删节)
在这部由Adam Driver和Marion Cotillard主演的《安妮特》中,卡拉克斯的多数灵感体现于装饰、场景和细节中。
当马丁·斯科塞斯认为超级英雄电影不是“电影”(cinema)时,他指的不是其故事情节,而是其制作模式:过度的管理、受制片厂控制的专营权的开发和保护,即“知识产权”。
但艺术的自由不仅表现于没有合同约束,与之同等重要的是内在的自由——一个导演准备冒着违背商业的风险去制作一部电影。
尽管独立于片厂制度外,但很多导演却像头脑中有制片厂那般进行电影创作。
莱奥·卡拉克斯的《安妮特》,是一部根据Ron和Russel Mael兄弟(他们又被称为Sparks)的相关故事改编而来的歌舞片,Sparks兄弟同时为本片创作了歌曲(卡拉克斯在此基础上额外加了几句歌词)。
从很多维度上看,这都是一部出色而大胆的影片,然而它并不令人完全满意——它并未像卡拉克斯最好的影片那般重构了电影的诸多可能性,因为卡拉克斯头脑中的制片厂由Adam Driver投射出来。
影片开场时,一个像卡拉克斯的声音如是要求观众:不要 “唱歌、大笑、鼓掌、哭泣、打哈欠、嘘声和放屁”,他同时提醒人们,“观影过程中不允许呼吸,所以现在,请进行最后一次深呼吸。
” 卡拉克斯最先出现在银幕之上,他在Sparks兄弟进行表演的Santa Monica录音室中操纵着控制板。
卡拉克斯的女儿Nastya Golubeva Carax居于虚化的后景中,当卡拉克斯准备提示Sparks可以开始时,他叫女儿到他这边来。
Sparks兄弟以《SO MAY WE START》一曲回应了卡拉克斯的请求,和四位女伴唱一起离开了工作室,三个主要演员Adam Driver、Marion Cotillard和Simon Helberg先后加入队伍,这群人唱着舒缓的韵律穿越街道。
Driver和Cotillard接过他人递过来的衣服,变身为他们的角色,随后前往演出——亨利前往 Orpheum 剧院,安前往 Frank Gehry’s Walt Disney音乐厅。
这个开篇即本片欢乐氛围的顶峰,在一个重复乐段的快乐开场后,一个男性虚荣和傲慢的阴郁故事就此开始。
一个传统的带悲剧色彩的故事被解构成一个肆意毁灭的虚无故事和一个摆脱困境的道义故事。
故事有些薄弱, 大多数戏剧场景以洛杉矶和其周边地区为背景,用歌曲唱段表情达意,代替对话表达人物的内心。
亨利·麦克亨利(Driver)扮演的“the Ape of God”(猿神)是一位轻微有些冒犯、世界闻名的脱口秀演员,他在开场前遇见Cotillard饰演的角色安,并与她坠入爱河。
安是一名歌剧歌手,Simon Helberg扮演她的伴奏。
安和亨利很快结婚,并共同抚养一个叫安妮特的小女孩,然而这段关系却摧毁了亨利的个人生活和工作。
他为自己被家庭驯化感到难过,随后在表演中变得异常冒犯。
结果他的事业一落千丈,而安的事业一飞冲天。
他变得自我放纵、鲁莽、暴怒,最终导致安死于事故。
由亨利抚养的安妮特是一个神童,一个天赋异禀的歌手,亨利不断剥削自己的孩子,最终她成为了公众人物和国际巨星。
但是(避免剧透)亨利挥之不去的狂怒,让在他迫切需要安妮特演出继续下去以养活自己的时候,他却犯了罪。
亨利是影片的中心人物,但是他在影片中的作用却出奇模糊。
安妮特是类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心理描写的角色。
从这个角度看,《安妮特》既类似于世界电影中最伟大的一部电影之一的《扒手》,又与之相抗衡:在这部罗伯特·布列松在1959年完成的作品中,一个哲学罪犯有意反抗,最终在历史性的最后一幕中,通过爱最终找到一种净化和升华的救赎——《安妮特》的最后一幕明确与之呼应。
布列松影片中的主人公在对话中透露了他的动机,但是亨利仅仅通过他在舞台上的咆哮和他简单的戏剧性行为中,稍微暗示了他对内心的纠结。
他的歌曲几乎没有心理描写,只是明确的动机声明,唯一例外的是他提到的“深渊”和他对自己致命行为的凝视。
这是一种夹杂着手势的模糊评论,他同时赞美又轻视反英雄人物。
这种戏剧性的朦胧要求表演的阐释,即导演和演员的基本协作。
这种关系是《安妮特》的核心;也是为什么本片有所有卡拉克斯影片的优点,却远未达卡拉克斯的最佳水平的原因。
卡拉克斯在几十年前的一篇采访中说,拍电影最大的特权是能与演员一起工作。
他成就了一些演员,贡献了 Julie Delpy 和 Denis Lavant (德尼·拉旺)的银幕处女作,还将Juliette Binoche(茱丽叶·比诺什)送上神坛。
在与他们的合作中,他们是卡拉克斯艺术的化身,卡拉克斯能自由拍摄他们。
恰恰相反,在《安妮特》中,Driver(同时也是本片的制片人)是明星,而不是卡拉克斯的作品。
卡拉克斯表示,在观看了Driver在Lena Duham的《都市女孩》中的突破性表演后,他选择了Driver出演自己的影片。
但《安妮特》的拍摄工作被延期,直到Driver完成了《星球大战》的拍摄。
与此同时,Driver还在斯科塞斯、科恩兄弟和鲍姆巴赫等人的影片中出演主要角色。
Driver已经开始同时代表主流好莱坞的神话和权威以及电影经久不衰的艺术传统。
这样的双重光环似乎阻碍了卡拉克斯的创造。
亨利这一形象可以背嘲笑、被不尊重、甚至被轻蔑,但卡拉克斯却同时给予这个故事,特别是这个角色一种虔诚的尊重。
结果,他给人留下一种在展示Driver而不是改变Driver的印象。
部分问题出在Driver作为一个表演者优势的性质上。
拉旺是《神圣车行》等几部卡拉克斯影片的主角,他像是一个虚拟变色龙,其转变首先是身体上的,就像 Lon Chaney和 Emil Jannings 那样的无声电影演员一样。
拉旺还是一名真正的杂技演员,即使在休息的时候他依旧在运动。
相比之下,Driver表演风格的独创性在于它经典好莱坞的特性:Robert Mitchum和Robert Ryan 一样,Driver总是无情地在展现自己,表现出与他合作的导演会喜欢的样子,这反过来又变成他在演他自己。
然而,拉旺的表演是内化的和象征化的,有没有夸张的装扮都不会影响他的卓越表演,而Driver是外化的,戏剧化的,文字化的,与现实主义表演密切相关。
Driver自己解释了他在《安妮特》中的表演悖论:“即使它看起来超现实,我也不能表现出超现实。
”所以,对Driver的转变和亨利内心活动的揭露完全落在了卡拉克斯那里,但是卡拉克斯从未足够接近Driver(无论是从文字,还是镜头,形象和戏剧角度),以突破Driver令人熟悉(尽管是很好的)的举止,并使演员臣服于自己的引力场中。
卡拉克斯怀着对Driver同样的敬意对待Sparks兄弟的歌曲,这同样也证明一种局限性。
某种意义上看,音乐家是导演艺术最严厉的考察,因为音乐的效果会违背导演的创造——音乐家做了很多艺术性的创造,导演往往选择中立,仅仅以纪录片的方式记录声音,唯恐自己的电影图像被认为妨碍了音乐艺术。
《安妮特》中,卡拉克斯拍摄的演员主要在长途旅行镜头中歌唱,这不太能揭示演员和导演的性格。
卡拉克斯没能使表演者的存在隐约可见,或者看起来冲出屏幕,他甚至不能很好的运用歌声。
关于这点,让乐器演奏家的声音像古典好莱坞音乐家那样进入配乐,其效果既非完全写实,也非完全的风格化。
歌曲片段有一种强制的、去掉个人情感的谦恭。
相反,《安妮特》的大部分内容都可以用一个致命的词总结(这表明卡拉克斯对编剧、作曲家的自我克制):说明性的。
尽管如此,卡拉克斯的说明与其他任何电影创作者相比,显得充满活力而诱人。
在他们早期短暂的浪漫时刻,亨利河岸在阳光普照的森林中,以“我们彼此如此相爱”为主题,演唱了一首伤感的二重奏。
亨利身着红色T恤,安身着黄色裙子,以一种如糖果般一样穿透自然。
随后,当安在亨利前面,亨利的双手凶狠地伸进取景框。
然后温柔的放在安的肩膀上。
本片的一大精彩之处是这对夫妇在游艇的甲板上遭遇的大风暴,卡拉克斯和摄影师Caroline Champetier 一起,拍摄出了惊心动魄的、戏剧动作和特效相结合的、和能够唤起经典无声电影巨大魅力的场面。
在描述宝贝安妮特的环球旅行时,一系列视频片段表现了亨利、安妮特和伴奏家的光彩照人。
亨利作为罪犯的一系列镜头以一种令人不安的角度展现给观众,而亨利受到惊吓后一个非常短而不稳定的倾斜特写表明。
可惜的是,电影中缺少类似的大胆的镜头特写。
但是,卡拉克斯在《安妮特》中的多数灵感,展现于场景、装饰和细节。
亨利从安分开的双腿中抬起头演唱的性爱场景,确实令人惊奇又疏远,亨利的表现并非痴迷或者享用,而是古怪。
宝贝安妮特由一系列木偶来呈现,她们的脸总会让人想起拉旺。
每次看见安妮特,总会让人产生一种晕眩的快感,但是卡拉克斯没有很好发挥这个技巧。
尽管安妮特是主角,但是孩子的心理活动和那些洋娃娃一样难以理解。
卡拉克斯同样没有走进安。
《安妮特》是一部关于亨利的电影,通过亨利的人物弧线,卡拉克斯迫切的表达欲被Sparks兄弟的故事所满足——但是,二者没有相互促进,反而是相互抑制。
穿着搏击手的连帽长袍的亨利,最先是舞台上一个可爱的存在。
他总是对身边惯常事物的抱怨(比如烟雾)
并以此自嘲他的本职工作
亨利像Lenny Bruce挥舞他的审判记录一样挥舞着自己的合同
他像一个洒圣水的牧师一般摇动着自己的麦克风。
亨利像Lenny Bruce挥舞他的审判记录一样挥舞着自己的合同,但是又不像Bruce,他从未深入任何细节,仅把文件作为一种道具(亨利随后采用了bruce的另一个举止,他像一个洒圣水的牧师一般摇动着自己的麦克风。
)《安妮特》证明了一个隐匿的选角格言:永远不要让一个非喜剧演员来扮演喜剧演员,因为好笑等同于会唱歌,好笑的是,当一个演员学不会幽默,也就不可能把其他人的幽默驾到配乐中。
Driver以游戏精神投入亨利的表演,但是呈现出的,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却不是喜剧人物。
相反,他只是表现得像喜剧人物。
“我将目光投向深渊。
” 当亨利的职业开始走下坡路,他的愤怒却与日俱增,他让安感到害怕,他在拉斯维加斯的低端剧院开玩笑说要杀了安,这确实冒犯到了观众。
亨利最终解释,他转向现实暴力的方式是他对“深渊”的屈服:“我将目光投向深渊。
” 也许,让这样一个艺术家说出他(总是“他”)在深渊中看到的真相需要勇气。
也许他舞台上那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对深渊的凝视,表现的是现实中的危险——一个充斥着骇人听闻想法的艺术家禁不住讲这种想法付诸实践。
也许是社会(更常见的是,女性)为了揭露这些可怕的真相而作出的不公正的牺牲。
也许这种恐怖的循环本身就是深渊,男性虚荣和暴力的真相,最终(剧透警告)让安妮特为自己在大众面前的消失做出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她从一个服务于父亲剥削需要的傀儡,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小孩。
《安妮特》既是对狼狈的自大男艺术家的赞颂,又是对他的否定;既是一出非道德的戏又是道德的剧,一个通过歌唱隐喻,让个人救赎和社会净化的寓言。
安妮特,而非亨利,是本片中最勇敢的说真话者。
她超自然的天赋、优美而无言的歌声,不是抽象美的飘渺形式,而是竭力表达还未获得语言的恐惧——这为她创造了听众,听众也成了当她终于能够用语言表述自己的恐惧时的见证者。
这个概念非常棒,Sparks兄弟和卡拉克斯非常真诚地将其表现出来。
但是,当缺少了卡拉克斯那典型的无拘束的想象力和与表演者的坦诚对抗,《安妮特》不再缺乏经验,却只是一个概念。
2 ) 形式碾压,剧本失控
这大概是今年观影在形式上最有突破最有意思的影片之首。
卡拉克斯的鬼才思维把这个彻底扑街的剧本赋能了几乎无限的能量,卡拉克斯试图把舞台剧和电影混淆在一起,在加上强制性的把观众拉入整体叙事当中,而这两点从影片第一秒就开始就在构建。
影片第一场戏就把接下来所需要构建的一切条件仅通过每一个人包括导演、编剧、主演、导演唱着走出录音棚这一个行为完成舞台剧上幕感、接下来歌剧化叙事方式的颠覆,怪异且合理化的感觉直冲脑门,叙事高效性到恐怖的境界。
第二幕则是先把语言带到舞台上,开始有意的颠覆语言与歌曲的方位且强制的让观众参与其中,群众的煽动性在这第一次呈现,在接下来的全片这种煽动都是演说者、媒体赋予影像内部的观众情绪,而影像外部也同样的被给予影响,但到了新闻片段采用虚拟背景后我们还是存疑的,这里用来抨击传播媒介也显得非常高效。
只可惜这样的调性只保留到了前半段。
第二段指挥家出现后影片的剧本着实有点失控导演把强烈的个人情绪注入了影片当中。
虽然在技法上沿用更加强烈的电影技法,但可惜表层剧本还是有点一塌糊涂。
只是直到最后一场戏女儿的真身出现才扳回来一点点明确主题含义。
本片的视听手法可以说非常非常 old school 非常多蝶化蒙太奇来制造复古感。
但其实导演是完全可以高效精准的调动观众,可能要贴合舞台剧才选择出本片的调性把。
而绿色意和红色作为男女意识来交互冲撞
3 ) 童话意志和音乐感官
起初我以为卡拉克斯想用“乐性”来代替对象世界里的“德性”,使之成为我们的判断法则和行为准则,但随着电影推进,我发现改变的不仅仅是对象世界的质料,还有现象世界的形式,按照我们在对象世界里培养出的思维准则我们会自发地进行对象符号化并解读符号,分析性地说清楚每个对象普遍性的本质和排他性的特质,然后综合性地理清楚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象在那个现象世界里的价值前提,总之,无论是感性直观到的,还是知性整理到的,这些都是经验性的,但经验性这种特质并不是电影本身所包含的,而是针对观众和银幕之间的关系的,毕竟这些都是对象世界里的实体,所以,只有消灭观众和银幕在对象世界里的实体,电影才能纯粹地展现它自身,不过,作者并不想暴君式地消灭观众和银幕,而是让观众和银幕自明地脱离实体——控制你的呼吸,进而削弱你的官能效应和工具理性,当所有的官能效应和工具理性都被消灭时,观众的主体只剩下了无限制地被视为单纯的童话意志,银幕被精简化为能直接与主体交流的音乐(在对象世界里能越过所有感官与主体直接交流的只有音乐)。
在这样一个没有目的、只有形式的现象世界里,“银幕”(音乐)不再是“观众”(童话意志)的工具,而是“观众”的诸原理之和。
作为童话意志的唯一官能效应,它可以被称作“音乐感官”。
但是当我们从电影里脱离出来写影评时,我们又不可避免地回到经验性的思维固着中,为了在写影评时不违背电影的精神内核,我们需要完成两个任务:1.解释“音乐感官”在对象世界里是如何可能的。
2.详细地展现“音乐感官”在电影里的那个现象世界被主体规定为对象世界过程中的经验。
1.音乐感官在对象世界里是如何可能的?
音乐感官是童话意志的唯一官能效应,按照感性范畴的概念:有机体的器官与目的一一对应,即主体的价值在于其目的的实现的概率。
但童话意志本身是形式的,而非目的的,因此音乐感官并不是某种目的的工具或是某种思辨的价值前提,而是感性的纯粹产物,之所以称之为一种感官,是因为在感性的范畴内,官能效应比理性更具有规定性,仅此而已,并不是说音乐感官具有感官的普遍目的性。
但也有人怀疑,音乐感官的目的不就是规定电影中的那个现象世界吗?
其实这种怀疑只是我们在对象世界里思维功能固着的产物,在对象世界里我们有多种官能效应,在它们帮助主体实现目的的同时,也给童话意志造成了很多主观限制,在当今对象世界我们所面对的最大的主观限制就是机械功利主义伪造的辩证法,它让目的在主体里的价值超过了意志,但主体在现象世界里不会遇到这些问题,因为现象世界的背后是超感官世界。
超感官世界排他、排己、没有时空规定性,可以排除音乐感官的所有主观限制,同时并不会对作为表象的音乐感官施加影响,无意间(不带任何目的性的成分)排除所有与音乐感官无关的杂多,使它能够像一门科学一样独立存在,还能保留它所包含的质料,这也是为什么音乐感官能够在没有感官的普遍本质的条件下被称为一种感官,而音乐感官在所有感官中唯一可以是超感官世界里的表象的原因则是音乐的特质:音乐是力的确定过程的永久形式,它在灵魂深处希望得到伸张,它无法平静,更从来都不曾平静过,它的非实体性和力感的有机结合体在告诉我们:世界是没有目的的、没有最终状态的,而且无法达到“存在”的程度,世界的一切表象都在它内在生命的黑夜,能符合如此特质的世界就只有超感官世界,而超感官世界就在影片所展现的那个现象世界的背后,直观地说,假如电影里的那个现象世界是一座城堡,卡拉克斯就是城堡的主人,他在电影开始时通过城堡的唯一窗户(声响)给了我们城堡的钥匙,即音乐感官,我们在确认了钥匙的准确性和效用性后打开了城堡的大门,大门上的锁就是超感官世界在对象世界里的表象,而真正的超感官世界则在城堡深处,虽然我们没有和它有直接接触,但它一直在吸引作为童话意志的主体的我们。
下一个任务中我们要完成的是详细地展现音乐感官在电影里的那个现象世界被主体规定为对象世界过程中的经验,这里的经验并非个体的,而是一般童话意志普遍拥有的经验。
2.音乐感官在电影里的那个现象世界被规定为对象世界过程中的经验 规定现象世界里的表象的主体并非一般个体,而是普遍的童话意志,规定的根据不是理性,而是作为官能效应的音乐感官,在音乐感官的范畴里,Ann被规定为可能作为目的的音乐感官,Henry被规定为作为形式的音乐感官,conductor被规定为音乐主体,Annette被规定为音乐感官在超感官世界里可能存在的形式,即纯粹音乐感官。
在展现可能现象的舞台上,可能作为目的的音乐感官符合了一般观众在对象世界里的思维功能固着,即在感性范畴内器官与目的一一对应,而观众很容易相信音乐感官的目的就是“悲剧性地消亡、神话性的虚无,最终仅存眼泪”,似乎音乐感官在所有感官中的特质就在于它的目的是虚无与激情,而其它感官的目的是机械功利与存在,倘若真是如此,卡拉克斯没必要单独抽出我们的音乐感官,只需要制作一部让人潸然泪下的情节剧即可,更没必要专门表象一个现象世界,因此,在现象世界里是不可能有作为目的的音乐感官的,只有作为形式的音乐感官(Henry),他借助超感官世界的表象(海上风暴),作为形式的音乐感官杀死了可能作为目的的音乐感官,在舞台上获得了独裁的权力,即童话意志只能通过作为形式的音乐感官才能认识现象世界里的经验。
但在离开展现可能现象的舞台后,可能作为目的的音乐感官的表象依然存在,她和作为形式的音乐感官综合性地证实了纯粹音乐感官(Annette)的表象的实在性。
为了能够将纯粹音乐感官的质料直观化,作为形式的音乐感官杀死了作为音乐主体的conductor,夺取了音乐主体的权力,在夺取了舞台和音乐主体的所有权力后,结合了童话意志和权力意志的音乐感官在现象的所有可能范围内展现纯粹音乐感官的质料,但是当纯粹音乐感官也被规定为音乐主体时,其质料背证明是不可能的,所有的规定也就失效了,可能作为目的的音乐感官变回了对象世界里的Ann,作为形式的音乐感官变回了对象世界里的Henry,音乐主体变回了对象世界里会动情、会批判的作为一般个体的conductor,一直像提线木偶的纯粹音乐感官变回了对象世界里的Annette——作为一般个体的Annette,我们观众也回到了对象世界——带着对探索超感官世界失败后的失望情绪回来的。
Ann、Henry、conductor、Annette、观众,我们都是对象世界里活生生的人,回忆了一次在现象世界里的梦,回忆中,“音乐”也变回了“银幕”。
4 ) 木偶的自醒
胜闻安妮特今年在戛纳的时候就褒贬不一,一直说想看,好不容易看了,然后看了一眼导演,终于明白了为啥如此两极分化,当年他的《神圣车行》是让我看了5次才依稀看得懂一点边的电影,十年相隔之作,直接用一种极夸张的形式、极熟悉的色调和镜头运用来亲昵而又反讽观众。
电影的开篇,卡拉克斯和她的女儿坐在掌控台前询问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然后就各种舞台上的表演者走出录音间,走到幕后,走出戏院或者录音棚,在街道上表演,一个完整的长镜头和红绿极强对比的冷暖差最后在警车的鸣笛声转向男女主摩托车和房车的背道而驰,敏感的我虽然想到最后他们这甜美的歌声和组合也许终将背道而驰,但是也仅是如此,后面的惊喜更大。
男主亨利作为脱口秀的顶流与女主作为音乐剧的顶流相爱、结婚、生子了,男主是用不断的挑畔和冲突让观众逗乐,女主则是用不断的戏剧里的死亡让观众相信并爱上她,两个人完全不同的自我表达和渲染方式,无一不在利用着观众甚至是人性的弱点,也在互相试探着对方的底线。
终于男主有一天失去了生活里快乐的源泉不能再被观众喜欢而被谩骂退出舞台时,女主也即将失去这生活的纠缠,以一种被男主失手推下大海的方式,留下了一个木偶人形的女儿安妮特。
我曾一度擦亮自己的眼睛看清安妮特木偶般的关节与脑袋,也一直在想象着这个如木偶般孩子存在的意义,终于在安妮特张嘴高歌后恍然大悟,这便是女主死时所说的用一生来纠缠男主的怨念附体啊(突然感觉在看灵媒)然后我就一直不肯直视了,毕竟小时候被切尔诺贝利的俄罗斯洋娃娃吓哭过一周。
后半程我实在是不知道说啥,音乐在重复,男主利用女儿到处巡演获得收入的生活在重复,直到有一天安妮特对着大众说了一句,“爸爸,你杀人了”,直接将她那个做不了脱口秀演员做幕后的loser老爸(我可没有隐喻谁哈)送进了监狱,然后木偶人就变成正常的小女孩了,声线也恢复成了正常人的声线,意寓着她彻底摆脱了父母的控制,但这里又和导演想反讽观众有点儿矛盾,可能导演也仅仅只是想自省或者寻找出路吧,这儿的安妮特抵抗了父母双权不就是抵抗了导演的绝对话语权吗?
好想再有一幕,开头卡拉克斯的女儿坐在观众席上看着镜头里好像在控制着演员们的爸爸坐在掌控台边,但外围看着那就是个监狱的样纸,哈哈哈,是不是我内心过于黑暗了?
5 ) So may we start? No!
我为什么要花两个半小时看一部IMDB6.4豆瓣6.9的片?!
是为了那个拍过《新桥恋人》和《神圣车行》的卡拉克斯(这次拿下戛纳最佳导演)?
是为了这几年红到发紫的Adam Driver和不老女神Marion Cotillard(再添一个金球奖影后提名)?
是为了Sparks编曲和编剧的摇滚歌剧?
又或者只是因为我听的某播客某主持人的力荐?
反正我这会儿肠子都悔青了。
这么个虚荣、堕落、贪婪、绝望的大男主故事,被拍得如此破碎、怪异、肤浅、做作,最后我脑海中只剩下片名小女孩安妮特的恐怖谷效应了。
所以我的忠告是,当开头所有演员一起唱着《So May We Start?》向你走来时,要果断说 no!
6 ) 卡拉克斯:继续冒犯观众
法国“鬼才”导演莱奥·卡拉克斯最新的电影《安妮特》是一部歌舞片,还有什么比这更让我们感到惊讶的呢?
这位在近 40 年导演生涯里只拍过 6 部长片(外加数部短片)的导演,为何要“染指”歌舞片呢?
歌舞片并非一种易于上手的电影类型,如果不是常年浸淫在该类型里的导演,贸然出手,可能走向败亡的困局。
布鲁诺·杜蒙的《童女贞德》(2017)不正如此吗?
卡拉克斯能拍更多。
只是到导演生涯晚近,他才越来越慢。
拍成处女作《男孩遇见女孩》(1984 )时,卡拉克斯才23岁,远比同龄人起步早,而且才华更加横溢。
接下来的两部作品都堪称杰作:两年后的《坏血》(1986 )和备受好评的《桥上恋人》(1991 )。
不知道是野心勃勃,还是自我耗尽,之后便是越来越慢的拍片速度,到了“十年磨一部”的地步。
备受争议的《宝拉X》 在1999年推出,而被捧上神坛的《神圣车行》更是花了十三年时间。
《安妮特》的评价注定两极。
像卡拉克斯的所有电影一样,它标新立异,不向观众做出任何妥协。
既然卡拉克斯此前的作品已经如此出彩了,不戴滤镜观看《安妮特》是不可能的。
甚至很多人在没看过电影之前已经暗中做出了评价,这是很少一部分导演才能享受的殊荣,比如洪尚秀、阿彼察邦、滨口龙介……真的如此吗?
千万不要被偏见遮蔽眼睛。
相信卡拉克斯会赞同我的观点,将《安妮特》当作一部正常的电影看待。
《安妮特》是又一个讲述好莱坞爱情故事的电影,甚至与《爱乐之城》《一个明星的诞生》一样,也以歌舞片的形式呈现。
亚当·德赖弗饰演的亨利·麦克亨利(Henry McHenry)是一位幽默风趣的单口喜剧演员,她的妻子安·德弗拉斯诺(Ann Defrasnoux,玛丽昂·歌迪亚饰演)则是国际知名女高音,以壮观的死亡场景咏叹调闻名。
两人在生活里扮演完美的夫妻,随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安妮特出生,灾难接踵而来:安在海难里丧身,亨利入狱,安妮特也中止了世界巡回演出。
整个故事之所以俗套,一部分原因在于亨利与安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角色,这引发了三角恋情和情杀的猜疑。
西蒙·赫尔伯格饰演负责安排安所有音乐的指挥,是安的前任。
当亨利发现安妮特身上的歌唱天赋,将其变成一棵摇钱树,在世界范围巡演。
指挥教安妮特弹奏母亲生前的歌曲,引发了亨利的嫉妒,失手杀死了他。
三角恋情并未超出我们的想象,甚至情杀、报复,也在套路之中。
在卡拉克斯的电影里,爱情意味着毁灭,《安妮特》也是如此。
对于剧情,我们或许不该过分关注。
毕竟这是两位摇滚乐手攒出的局——罗恩·梅尔 (Ron Mael)与弟弟罗素·梅尔(Russell Mael)组成的花火乐队(Sparks),既为本片撰写了剧本,还负责全片配乐——我们并不清楚卡拉克斯在剧本上插手多少,至少从资料上看,此前所有的电影都由他本人单独操刀。
因此《安妮特》显得很不一样。
最大的不同在于,卡拉克斯失去了对影像的全权掌控。
对于一位个性极其鲜明的导演,这也许会导致风格部分让渡。
在《神圣车行》里,我们见证了导演意识彻底贯注到影像里,会走向何种境地。
影像事无巨细、挥洒个人才华的极端控制,导致演员(德尼·拉旺)如同可被任意丢弃的傀儡,受尽“摧残”。
这是那类天赋异禀的导演惯常采用的方式,譬如奥逊·威尔斯。
既是才华横溢的自然结果,也在结出自噬的恶果。
《安妮特》长达2小时21分钟,充斥着实景的脱口秀演出、夸张的歌剧表演,以及依循歌舞片套路不时响起的曼妙歌声。
冗长、松散、凌乱,是我们能找到的词汇,自然无法与构思精妙、密度高强的《神圣车行》相比。
《安妮特》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虽然在肥皂剧情的背后,裹藏着导演对于现实与表演、真实与虚构、演员和观众、傀儡替身等话题的探讨,但深度或许不及《神圣车行》的零头。
玩弄真实与虚构、真相与谎言,是卡拉克斯惯常探讨的主题。
《安妮特》一开场,作为导演的卡拉克斯与女儿Nastya坐在屏幕前,指导着录音棚里的梅尔兄弟录音。
这是整部电影的开场秀《让我们开始吧》(So May We Start),随之,歌手、乐队、技术人员都站起身来,离开演播室,走上街道,主演亚当·德赖弗和玛丽昂·歌迪亚也随之加入。
这个时候,电影已经开始了吗?
出现在银幕上的是作为演员的亚当·德赖弗、玛丽昂·歌迪,还是他们在戏里的角色亨利·麦克亨利、安·德弗拉斯诺?
卡拉克斯在此玩了一个鬼把戏,让现实走进了虚构,打破了两者的界限。
很显然,卡拉克斯有志于将《安妮特》变成一场盛大的演出。
片头字幕还在播放的时候,他已经耐不住性子,用第一人称邀请观众做好准备,并集中注意力参与其中——“女士们、先生们,请你们集中注意力,如果您想要歌唱、大笑、鼓掌,哭泣、打哈欠、喝倒彩或放屁,请您在脑海里做,想想就好,敬请各位保持安静,屏息直至演出的最后一刻,演出过程中禁止呼吸。
因此,请您现在深深地吸进最后一口气,谢谢!
”这种自反的思路让我们想起《神圣车行》类似的开场:一位观众在黑暗的电影院里,等待演出来开始,然后就是整部电影。
德尼·拉旺扮演的奥斯卡现实坐在一辆白色加长豪华轿车里,穿梭于巴黎的街头巷尾,为着不同的“约会”变换自己的身体。
与《安妮特》类似,《神圣车行》同样也可以看做一场场演出片段的集合,为了完成一种多向度的、类百科全书式的表达。
银幕/屏幕的内与外,录音棚的里与外,脱口秀与歌剧舞台的上与下,都在指向观看与被看的逻辑。
一切都是表演。
亨利在脱口秀舞台上通过抖露隐秘的私事,来唤起观众的热情,甚至在装扮上,他也有一种“暴露癖”:从连帽浴衣下露出紧身平角内裤,和一副健硕的肉体,一边表演遭受枪击让观众信以为真,一边假装泄露自己用挠痒杀死了妻子,让观众获得过山车般的激情体验。
与舞台上自恋、激情、张扬的表演相类似,生活中的亨利也像是个 “戏精”:在城市街道上飚速骑摩托,穿连帽浴袍四处走动,懂得在恰当时机借着镁光灯给妻子一个拥吻。
甚至连做爱时,两人都是唱着歌的(《我们如此相爱》,We Love Each Other So Much)。
对于媒体来说,亨利与安在日常生活里的一举一动都是报道素材,能够迅速转化为新闻呈现在荧幕上。
这难道不也是走秀?
只不过演出舞台延伸到了整个世界。
说白了,歌舞片这种电影类型的实质,在于能将现实世界转变为舞台。
既然角色能在任何场景里都能高声唱跳,那么也就没什么是现实的。
一切都是虚构,而真相只有在谎言的构成中才能被揭露。
亨利说他用饶痒杀死了妻子,没有人会相信,但在这个谎言里,确实暴露亨利有杀死妻子的动机。
台下的观众问过亨利为何想成为脱口秀演员?
亨利回答说:“这是我知道的唯一能说真话的方法。
”亨利讲出真话的办法是冒犯观众,惹怒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让观众获知真相。
这看起来有些“残酷戏剧”的特色了。
相较而言,安用美妙的歌声安抚观众,让他们受刺激的神经重新安定下来,获得新生。
正如亨利自己所说的,他杀死了观众,然后妻子安再把他们复活。
作为冒犯观众的代表导演,卡拉克斯自然不会认同歌剧,而是站在脱口秀这边。
脱口秀与歌剧,代表着两个相隔久远的的年代里两种大众艺术;亨利与安的结合,是当代世界与前现代世界的汇合,内部暗藏着不和。
亨利“杀死”了安,正如脱口秀在与歌剧的搏杀中取得了胜利。
现实世界的人更加喜爱歌剧,而不喜欢冒犯之言(脱口秀),因为群众总是安于现状,逃避现实。
这也是电影结尾面对安妮特的指责,亨利反复强调“理智孱弱,想象力无穷”的原因,是群众无穷的想象力杀死了亨利。
亨利看似玩世不恭,实际上一直在告知观众真相,但观众并不想接受真相。
继而在安死后,亨利开始自己制造幻觉,操控安妮特(提线木偶)成为赚钱工具。
亨利也以幻觉的形式迷惑了公众(如同安),当安妮特觉醒后,亨利遭遇了反噬,这是他死亡的原因吗?
金·维多《群众》(1928)最后一幕金·维多的名作《群众》最后一幕出现在《安妮特》里,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镜头从上到下扫过,观众在电影院里放声大笑。
这种无差别、同频率的大笑,让人胆战心惊。
“群众”作为集体,表现出了同一性,正是“乌合之众”的要义。
同时,它也指出群众通过沉迷在幻觉中(在电影院里大笑)逃避了现实。
电影、歌剧、脱口秀……所有艺术都在制造幻觉,让观众沉迷其中,看不清现实世界的真相。
对中国观众来说,歌舞片并非易于接受的类型,我们欠缺相应的文化土壤。
除非是热爱电影的影迷,普通观众大概很难注意到《安妮特》。
这在很大程度上让这部电影避免了误解,虽说,随着时间的流逝误会必然会发生,因为“群众”的眼睛并非雪亮。
我估摸,《安妮特》将成为卡拉克斯迄今为止评价最低的电影,最后的豆瓣评分不会超过7分。
7 ) 看到结尾,终于等到她黑化了
大家好,我是戴着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片片。
近年来,说到“歌舞”和“电影”两个关键词,估计不少人想到的都是印度神片。
一言不合就载歌载舞,已经成了印度电影的标志。
除了印度开挂神片,还有一种音乐剧式的电影,近年来逐渐步入观众的视野。
通俗一点来说,这类电影从头唱到尾,中途的对白很少。
著名的比如蒂姆波顿的哥特风电影《理发师陶德》,以及音乐剧改编而来的《悲惨世界》等等。
歌舞表现形式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情感更有张力,奔放的更奔放,压抑的更压抑。
如果用歌舞为载体,讲述一个心灵扭曲的杀人凶手的故事,岂不是很炸裂?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开幕影片《安妮特》,讲述的就是个暗黑爱情童话。
简单说一下剧情。
男主是个单口相声演员,开场的时候,他穿着一身绿色浴衣,走上阴暗压抑的舞台,表演(似乎不那么好笑)的喜剧片段。
台下有观众问,你为什么成为喜剧演员?
男主说出自己对喜剧的看法:
残酷的事实如果通过喜剧的方式说出来,观众只会发笑,而不是追究。
男主的妻子是一个女高音歌唱家。
在媒体的镜头前,两人恩恩爱爱;可背地里,夫妻俩日子过得并不安逸。
结婚没多久,他们有了孩子,并为孩子起名安妮特。
可男主刚要承担起父亲的责任,妻子就出轨了。
原谅出轨,活得像鬼,更何况像男主这样压抑的人,怎么可能原谅。
在一次表演中,男主在舞台上吐露心声:“我杀了我的妻子”。
虽然他现在这么说只是发泄,可并不排除,他真有想要杀妻的想法。
接着,男主一人分饰两角,开始表演杀妻一幕。
他抓住妻子的脚开始挠痒,挠着挠着,妻子就笑到窒息而死。
这段表演很炸裂,大概胜过他之前所有的表演。
可这一次,男主并没有给观众带来欢乐,而是引发了全场唾骂。
观众只愿意看戴着小丑面具表演的他,可真实的他是什么样的,who cares?
再看看妻子这边。
影片用了“女同胞劝告的方式”,展现妻子出轨后内心的摇摆不定。
无论是爱上心理扭曲的男主,还是自己的出轨之举,都无异于飞蛾扑火。
丈夫开车的时候,妻子坐在后座上,恍惚间,她看见一辆摩托撞了过来。
妻子一个激灵瞬间惊醒,原来只是做梦。
可这个梦也暗示出她此时的心理:对丈夫失去信任,甚至心怀恐惧。
夫妻俩之间已经有了隔阂,但作为备受瞩目的明星夫妻,面子还是要做足的。
在媒体的镜头前,两人继续秀恩爱,并决定乘坐游艇度假。
原以为是风和日丽的度假之旅,可出行当天,海面上巨浪滔天,狂风骤雨,整个就一灾难现场。
再加点冰山,可以演《泰坦尼克号》了。
夫妻俩来到游艇甲板上相拥共舞,舞着舞着,男主一脱手,将妻子甩进海里。
这段在暴雨中的双人舞气氛炸裂,男女主矛盾爆发到了极点,海报画面用的也是这个场景。
等暴风雨过去,男主在岸边醒来时,身边只剩幼小的女儿。
妻子的魂灵出现,来了一出猛鬼附身的戏码。
妻子恶狠狠地说:我会通过安妮特,日复一日地缠着你。
在所有人面前,男主谎称妻子之死是一场意外。
接下来,另一个重要角色正式登场,妻子的外遇对象——小三。
小三这张脸十分眼熟。
没错,在《生活大爆炸》里,他是笨拙的工科男霍华德。
在这里,他摇身一变,成了满脸深情的第三者。
得知女主死后,小三看起来比男主还心痛一百倍。
这大概才是传说中的真爱吧。
导演用了一个不断旋转的镜头展示小三,每旋转一次,他的感情就激烈一分。
可再到展现男主的时候,只是用一个固定的镜头,拍摄他每天麻木不仁的生活。
吃饭,睡觉,喝酒,以及流程式地思念亡妻……
男主把小三当哥们儿,并不知道他是妻子的出轨对象,反而邀请小三来到家里,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由小三教安妮特唱歌,两个男人一起养娃,一起致富——将安妮特培养成童星,一手打造致富密码。
在男主眼里,安妮特只是发财工具。
她初次登台,台下不乏有质疑的声音,大家都看得出来,这是对孩子赤裸裸的剥削!
可没多久,舆论就转变了方向,大家开始欣赏安妮特的表演,观众们高呼着:“我爱你。
”两人的生意越做越大,所到之处,都有粉丝们的尖叫声。
通过剥削孩子,他们走上了人生巅峰。
直到这天,男主发现小三竟然在教安妮特唱妻子曾唱过的歌。
他很不爽,这是我和我妻子的歌,你没有资格教她唱!
小三随即而来的一句话,让男主原地破防。
我才是安妮特真正的父亲,这首歌也是我写的。
防火防盗防兄弟,防不住,就等着后院起火吧。
男主一怒之下,将小三溺死在池子里,房间里的安妮特看见了这一幕,面对凶神恶煞的“父亲”,她蒙上了眼睛。
杀人的事迟早会败露,必须带着安妮特远走高飞,在这之前,他让安妮特参加最后一次演出,对观众道别。
戏剧永恒的套路之一:最后一次,总会出事。
舞台上,安妮特沉默良久,对着所有观众说出了一句话:爸爸杀了人。
警察火速逮捕了男主,不久后,安妮特前来探监。
从头到尾,她始终受“父亲”的操控,所以导演用一个木偶孩子来扮演,可现在,她已经长大,自我意识觉醒。
这一次安妮特由一个真正的女孩来扮演。
她的眼神里没有宽恕,没有圣母心,她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这个男人。
最后陪伴男主度过余生的,只有妻子挥之不去的鬼魂。
豆瓣上,《安妮特》的标签,是剧情+爱情+歌舞。
纵观整个故事,它讲述的就是一个被生活与工作压迫到极致的男人,杀死妻子与小三,最终入狱。
爱情片未必就是甜美的,也可能是暗黑的。
如果光看影片海报以及一些现有的片段,很容易让人想到《爱乐之城》。
对比二者海报,都是男女共舞,一个浪漫温馨,一个疾风骤雨。
影片的色调,文艺的布景,载歌载舞的形式,恋爱撒糖的甜美氛围,这都很“爱乐之城”。
可我更愿称《安妮特》为暗黑版《爱乐》。
除了暗黑向的爱情故事,表演形式是《安妮特》最大的亮点。
导演把歌舞剧搬到大荧幕上,以电影的形式来呈现,最终效果介于歌舞剧和电影之间。
喜欢的人会觉得看《安》的时候,既像在看歌舞剧,又像是在看电影。
不喜欢的人则会认为导演野心太大,双方风格都沾一点,最终高不成低不就。
男女主二人,一个穿绿衣服,一个穿红衣服,这也暗示了两人的性格不同。
一个压抑扭曲,一个浪漫多情却不幸英年早逝。
不过,就影片绝美的画面,精彩的剪辑,故事详略得当的节奏来看,《安》无疑为戛纳电影节缔造了一个绝美的开场。
《爱乐之城》的结局,石头姐和高司令花开两朵,天各一方,当时看的时候有点意难平。
可后来才恍然大悟,谁规定甜甜的爱情片,就一定要有个百年好合的结局?
分开还能追求新的人生,起码比《安妮特》中杀疯一片要阳光得多。
《安妮特》用两小时的长度,拍出了四小时的既视感。
喜欢这种暗黑文艺风的小伙伴,点个赞,评论区里也能分享一些类似的影片。
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
拜了个拜本文图片来自网络编辑:大猩
8 ) 亨利的安妮特,即卡拉克斯的电影
荧幕上是转瞬即逝的绚烂与疯狂,而空间的底色由始至终是幽深晦暗的悲凉死寂——在《安妮特》与观众不断决裂的140分钟里,诞生的不仅是影像与音乐间交会的新维度,更是某种前所未有的电影触觉;而这也是卡拉克斯本人的脉搏,在美与深渊之间起伏,在荒诞中热烈地灼烧。
卡拉克斯与女儿在《安妮特》 《安妮特》直觉上的赤裸与古怪,首先来自其满溢的毁灭与拒绝性。
亨利的语言直白暴烈,时刻在逼近精神的赤裸、扒开观众与自己的外壳以展现虚无的本质;而他的表达却又总在最关键的位置含糊阻滞,显示出其对“被理解“的悲观与拒绝。
同样的,在当今观众预设电影中的歌舞应当避免断裂感地融入影像并从而构成“真实“的时候,卡拉克斯却悍然利用歌舞的离间作用,让剧院的氛围始终笼罩着影片,在开头的音轨与录音棚以及结尾的夜行处建立了肉眼可见的、出入电影世界的通道,再一次实现了电影层面的赤裸坦诚——观众显然是不会适应的,因为所有的类型片传统已经将电影孤立为一个“避世”的房间,而卡拉克斯企图寻找那扇门的位置。
承接《神圣车行》,电影亦把虚拟性、网络等多元媒介与“表演“之间产生连结的方式融入影像,将空中楼阁般的“电影”清晰地放置于资本与商业社会背景下。
于是,观众漂浮在传统的电影概念和现实之间,一个半寐半醒的虚空之中,被“拒绝”沉湎于任意一边,从而更加看见电影某个侧面的沉重。
还有无数异想天开的场景,如安妮特诞生,那突如其来令人倒吸冷气的怪诞人偶,是残忍与梦幻并存的符号。
卡拉克斯就这样以最华美的方式大胆展现人工与不自然,离间着观众、冒犯着观众,正如亨利在他的戏剧中不断地冒犯台下的观众,明白这种不适应对于观者来说是一剂特别的致幻药。
亨利的毁灭与拒绝性 尽管一如既往秉承新巴洛克主义的美感,《安妮特》已经不再像卡拉克斯早期的电影一样,充满速度、心跳般的节奏感与剪辑切换间惊为天人的细腻,镜头更长了,愈发连绵与稳健,甚至展现出一种倦意;卡拉克斯也不再描绘某个挣扎在黑夜与日光间的早熟忧郁青年,而是坦然地在酒神的疯狂中创造白夜。
《安妮特》中的毁灭与欲望,正犹如《宝拉X》的B面:年轻的皮埃尔在一片明亮宁静中无法控制地趋向幽深之处、自我放逐;而亨利似乎是个成熟的完全体,最终接受了自己就是那个被深渊吸引的人,如同一面诚实的镜子,无所谓是否在自我凝视中走向自毁。
他以恶魔的肢体悄悄地靠近画面中妻子的身体,在面对妻子“圣洁、害羞的笑“时混沌地冒犯,注视着“圣洁”与绝望的自我间的鸿沟。
爱情在这里又露出了另一副面孔:亨利与安是如此不同,他们的爱情正如歌词的咏唱,是无比反直觉且不可预料的,几乎“不可能”:喜剧男演员亨利,在辛辣与挖苦、真实与虚构的模糊中不断地挑战观众的认知和伦理底线,制造笑声的同时也激发了精神的悲痛欲绝;而悲剧女高音安,歌咏着仿佛日神一般优美的灵魂,在她演绎的故事中一次次地“死亡”,但表演与歌声却被认为是“拯救”了观众。
它们之间细腻的抵牾时不时在自述的音乐中展开,夹杂着影像中零碎复杂的信息,幻化为噩梦和车祸,最终走向风暴中的死亡。
或许《安妮特》的情感中有部分十分私人的投射,卡拉克斯对叶卡捷琳娜·戈卢别娃的离世,也是始终抱有悲痛、自责的情绪与 “不值得被爱”的自我怀疑。
令亨利与安感到窒息、失去欲望的拉锯,代表的不仅是爱情中的冲突力量之争,亦是电影乃至艺术中美的力量之争:荒诞黑暗又充满冒犯的粗俗“本能”,以及歌剧所代表的神圣信念和“非即兴”。
从《粪先生》起,卡拉克斯的作品有着愈发明显的、亲近滑稽剧的部分。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种拍摄的兴趣是一种必然,或许因为逗笑与讨好的荒诞永远伴随着一切表演和创作。
镜头中、座位上不断重复的机械的“笑“夺取了这个表情原本的意义,让喜剧演员变得面目可憎。
《安妮特》将这一悲剧感充分附着在亨利这一角色上,让他成为一个舞台上、生活中的小丑,在妻子所代表的“神圣价值观“的催化下,爆发出强大的毁灭欲。
安的演出、歌唱是为观众而死、漂亮地死;但对比下亨利渴望的显然是能杀人、直指深渊的赤裸创作。
亨利,或者说卡拉克斯本人,就此与观众决裂了。
他不但厌恶自己、厌恶观众,更厌恶彼此的关系。
他看清了一个受到热爱的人必然是一个永远需要隐藏真正的自己的人,因为在表演中说出实话是会被唾弃、带来麻烦的。
安这样的艺术家被怀念,在与观众的关系中却实则处于被剥削的状态;蔑视观众的亨利们,如若想要逃过自我毁灭的命运,也终会被驯服。
观众的笑声中隐藏着欲望和恶心,表演者们终有一刻在午夜梦回时恐惧这一切,无力地说出那句:Stop watching me.
即便如此可悲可嫌,在女儿安妮特身上,卡拉克斯依然展现了一种对“纯粹”无畏甚至病态的执着。
他化身亨利,注视着此刻充满利用与伤害的罪恶深渊,哪怕“杀死”她,也要将安妮特几乎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绝美展现给世界,告诉所有人,奇迹是存在的。
他必须这样去做,去战胜时间、对抗创作的“无意义”,毕竟如果在心的监狱那个没有杀戮的世界中,创造者只剩下漫长的时间。
当人间无边的黑夜中露出纯洁美丽的星月光辉,犹如虚无中有人开始相信电影的奇迹时,她便会带来绝世无双的、形而上的绝美——她是亨利与安的女儿安妮特,她是卡拉克斯的电影。
9 ) 三颗星不能多了
司机像《愤怒的公牛》拳击手一样穿着短裤和浴袍在台上走来走去唱歌说话。
敏感和暴烈的样子,真是注满了“拜伦”的灵魂!
被提及最多的开场几分钟!
说实话,这不就是我The Verve乐队几十年前的《Bitter Sweet Symphony》mv吗!!!
电影从华丽摇滚到迪斯科到电子再到歌剧,把所有元素融了个遍,其实这个创意本就更适合以原先的概念专辑呈现,真不太适配电影。
一旦观影时音乐的新鲜感消失,习惯了它不断的重复和反问表达的手段,就会马上意识到电影的空洞。
一会儿男主陷入metoo的谴责,一会儿和女主两人仿佛置身波塞冬历险记。
我都笑了哈哈,可能恰巧应证了导演想表达的悲剧和喜剧相生相依的点吧,很难分清两者的终点和起点在哪里。
当你看开场以为是《爱乐之城》的时候,看着看着就会发现其实是艺术版《一个明星的诞生》。
也可以算是《婚姻故事》的暗黑重复。
还夹带着《安娜贝尔》般恐怖的匹诺曹木偶孩子。
男主离开舞台时赤裸屁股背对观众,完全虚无主义的蔑视行为。
他说他杀了观众。
女主离开舞台时优雅的鞠躬,每晚在舞台上优雅的死去,被鲜花簇拥。
她说她救了观众。
艺术家的表达,究竟是想伤害观众还是拯救他们?
电影让我一度很分裂,音乐部分很强烈,似乎一直在表达的就是“别管评论家无视他们”的任性!
再回到电影本体行进时是“继续创作”!
整体观感真的不佳,但不代表不值得观影,毕竟我们也不是常常能看到这种超现实主义和前卫摇滚歌剧结合的电影。
10 ) 純吐槽了
1.說實話開場確實不錯,然後就每況愈下。
2. 2小時拍得像4小時一樣難熬想離場。
本來以為是我的問題,結果看完回想出了下面三四五六條,覺得還是片子本身的問題。
3. 作為一個musical全篇下來沒有一首動人的歌,真的是撐不起來。
短評裡面還有人說什麼覺得不好聽的人要怎樣怎樣,是多沒聽過好音樂和看過好musical。
自己品味如何不反思一下也就算了,一遍盲目吹噓,一邊排斥其他人的批評有何意義。
4. 整個故事就挺蠢的,看了看其他評論,說整個電影的音樂和劇本都是“由美国电子乐队斯巴科斯的创办人麦尔兄弟创作”,這兄弟看來得被我拉黑了。
當然,不出意料的,音樂搞成這樣的,又寫得出來什麼好故事呢(笑5. 歌迪亞和Driver之間沒有任何化學反應可言,整個戲拍得都很技巧,卻一點也不動人。
全片表現得好的竟然是生活大爆炸的Howard你敢信,雖然他戲份不多但也許他當主角會好很多,畢竟人家某種意義上是成功的喜劇演員。
這又要說到Adam Driver當脫口秀演員的部分真的一點也不好笑(get不到任何誇Driver的點,說實話我也從來不覺得他有什麼好的,長得又醜演技又浮誇,你們一天天吹他他會被捧殺的lol)。
6. 至於各種誇讚的想要突破musical的形式,想打破the theatrical和the cinematic之間的界限,看得出其嘗試,但明顯兩頭不討好,既不是很好的musical,電影感也有削弱。
7.那個布娃娃真的是一言難盡,也許也是想找一種布偶劇的感覺,但明明能有更好的視覺表達為什麼要用那麼 creepy的安排?
8.一星給開頭,一星給音效。
可整體平庸的音樂白白浪費了我昨日看片的那麼優秀的杜比影院。
9.一邊口一邊唱歌是怎麼做到的?
這裡的確印象深刻,外網有comment說Driver如何能控制呼吸的確有一套lol10. 曾經看電影給分很寬容,現在覺得確實如果不批評,則讚揚無意義。
憋著不吐槽也更是做不到。
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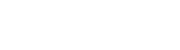














































































我觉得观影过程挺舒服的。看完后思考更多的是“反过来的戈夫曼拟剧论”,又回到那个导演(艺术家)与观众(欣赏艺术的人)之间的关系,创造与使用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上。
看来面对自己还是太难了。大开大阖的男主缺少细节设定,这很不适合给人感觉empty inside的Driver,他是那种你塞给他再多设定再多情绪他也能hold住的演员,但Carax需要的是拉旺或者比诺什那种自带蓬勃内心能量的演员,这个选角大失败,Driver当comedian实在说服力太弱了,empty inside的人怎么可能是comedian?可能Carax本来就有意模糊化了自己吧……开头还是不错的。
故事简单对于卡拉克斯本最不是问题,形式的、修辞的拉满即可。但《安妮特》在视听层面的捉襟见肘感太强了,音乐、哥特式人物和场面塑形皆是点到为止,没预算惊世骇俗,但天马行空棚拍总可以吧,没有都没有,好像钱都花在台下群演身上。虽然不至于又臭又长,但也真的乏善可陈。 @望京电影资料馆
好精致的诡异,有点恐怖谷,但这个鬼娃安妮特也正是男主对孩子认知的投射,拍的非常美,鬼绿迷人
看的时候想了无数次,这也许就是舞台音乐剧和音乐剧形式电影的壁垒,而卡拉克斯是想要打破它。
歌舞剧版婚姻故事
因为有亚当·德赖弗,电影给我一种莱奥·卡拉克斯用他的风格拍了一部《婚姻故事》的感觉,前三分之一还是有《神圣车行》的那股味,挺酷的,后面就的剧情脱缰了,疯得有点拉不住了,而且真的什么都要用唱的吗?连西蒙·赫尔伯格掉进水里快死了的时候的台词都用唱的,真的没必要,好好说话不行吗?
节奏拉胯,音乐也不突出,主演没精神,跟这片子五行不合
四星半。脱口秀喜剧演员与歌剧演唱家的悱恻爱情,缔结出怪诞之女安妮特,莱奥·卡拉克斯将一出三言两语便能说透的世俗往事,激活为天马行空的墨绿警世寓言。叙事的过程,成为各色舞台表演形式呈现的通渠,调度极尽复杂之能事。火花兄弟的作曲更成为影片的灵魂挽歌,在亚当·德赖弗声台形表样样通达的发挥下,令心酸成为终极魅惑。
I hear the stars laughing at me 若我也需要告解 可能会理解你更多
歌好难听哦,原来预告片就是整部电影的高光集合了🤮🤮🤮
只能当成一次大场歌舞情景再现 唱曲并没有在声效的加持下抓住人心 悬疑和温情的杂糅也撑不起想要呈现的奇幻味道
3-,也就是人的失落、失望、失控,毁灭之路。形式既不讨喜也不凌厉,不好看也不能突显主题。女人咬苹果,男人脸有疤。
想抓住什么对标否则无法形容刚刚看到了什么 像是大卫林奇抓着杜蒙拍了一部婚姻故事版的温蒂尼 再看预定
分明感觉卡拉克斯又失控了。弥漫全片的是一种矫饰的表层黑暗,相比眼花缭乱的形式,内核真是有点单薄,再加上找越来越明星化的亚当司机做男主,无论如何演不出来灵魂深处的黑暗可怖。2.5
GIVEN Prior (Carax + Musical film + Marion Cotillard) the Bayesian inference will tell... #Cannes2021
太煎熬了,两个小时感觉像四个小时。音乐剧也好,Stand-up comedy也好,一点光彩都没借上。有些实验性的东西真没必要做,甚至让人怀疑卡拉克斯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音乐剧,想必不是那么喜欢吧,要不然为何整部电影里没有一首歌称得上好听二字?最后一幕戏女儿的唱段实在太糟糕了,桑德海姆用脚趾头都能写出更好的歌。电影对Stand-up comedy的表现也毫无尊重可言,扛着红旗反红旗啊!Adam Driver每一场单口喜剧都能把我气得胃酸都反出来。成功唤醒了我大学时看孟京辉那些所谓先锋话剧的痛苦记忆,不禁令人想呐喊“导演呢?出来!出来啊!”。
差得令人发指。我不想去深究这片所谓的自反性寓意(如果有的话),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从头到尾都很空洞的把戏。卡拉克斯大概的确是老了,那股生蛮得足以直接创死观众(而不是在舞台上摆出冒犯台下观众的姿态)的力量哪儿去了?歌不好听倒还是其次。
下辈子投胎做Annette吧 屁都不干还被万人追捧 后半段那个舞台scene我tm一瞬间把中间的小丑娃看成kanye west
安妮的確被亨利殺了,就像瑪麗昂·歌迪亞的演出毀在亞當·德萊弗和導演莱奧·卡拉克斯共同製造的怪誕形態下。夢魘似的表演,前衛到令人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