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里卡奇遇》剧情介绍
艾萨克(利卡多·特雷帕 Ricardo Trepa 饰)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摄影师,一天,他接到了一通神秘的电话,电话那头的,是当地十分有名的富豪之家,他们向艾萨克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请求,那就是替家中早逝的小女儿安杰丽卡(碧拉尔·洛佩兹·德·阿亚拉 Pilar López de Ayala 饰)拍摄一副肖像。 艾萨克接受了这个充满了不详气息的委托,然而,当他亲眼见到安杰丽卡之时,却立刻被其完美无缺的样貌所俘获,他根本就不相信,眼前这个双眼紧闭一脸安详的的少女早已经香消玉损。之后,更为诡异的事情发生了,艾萨克镜头之中的安杰丽卡复活了,她化身成为不散的魂魄,日日缠绕追随着艾萨克。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迪斯科男孩机械画皮离家路远西线无战事娚的一生葬礼秘境我只喜欢你幻变梦境青春星主播之我的个女神啊脑中埋藏了智能手机能面检察官寻根海军陆战队员5:杀戮战场她的神话少年歌行最强番长是少女-GirlBeatsBoys-没有我的日子菜单虎山行择君记蜡笔小新:呼唤传说!三分钟嘎巴大进攻吊人游戏破裂小狗当家信访局长我最糟糕的朋友人民检察官翼·年代记上帝的笔误
《安吉里卡奇遇》长篇影评
1 ) 感触
很好看,能勾起童年的回忆该电影简介由豆瓣网专职人员撰写或者由影片官方提供,版权属于豆瓣网,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使用整体或任何部分的内容。
艾萨克(利卡多·特雷帕 Ricardo Trepa 饰)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摄影师,一天,他接到了一通神秘的电话,电话那头的,是当地十分有名的富豪之家,他们向艾萨克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请求,那就是替家中早逝的小女儿安杰丽卡(碧拉尔·洛佩兹·德·阿亚拉 Pilar López de Ayala 饰)拍摄一副肖像。
艾萨克接受了这个充满了不详气息的委托,然而,当他亲眼见到安杰丽卡之时,却立刻被其完美无缺的样貌所俘获,他根本就不相信,眼前这个双眼紧闭一脸安详的的少女早已经香消玉损。
之后,更为诡异的事情发生了,艾萨克镜头之中的安杰丽卡复活了,她化身成为不散的魂魄,日日缠绕追随着艾萨克。
©豆瓣
2 ) 古典精神——《安吉里卡奇遇》
葡萄牙著名导演曼努埃尔·德·奥里维拉2010年时已经102岁了,但他仍努力地拍着电影。
这位导演于1931年拍摄了纪录片史上的经典之作《多罗河上的辛劳》(Labor on the Douro River),此后一直在胶片上耕耘,历经默片、有声片、各国新浪潮,到今天仍守着自己的一方净土。
1981年、1985年和1990年,奥里维拉先后获得了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和戛纳电影节的终身成就奖。
他总是将深邃的思索与电影结合一处,他的所有影片早已连接成为一片思想花园,而这新近的一部《安吉里卡奇遇》,是花园中一朵新盛开的玫瑰。
影片的故事颇奇诡。
一天深夜,一个年轻的摄影师伊萨克被请到帕塔斯家族的大宅子里。
家族主人新婚的女儿安吉里卡刚刚去世,家中亲人悲恸万分,便请摄影师来为女孩儿拍摄最后的容颜。
女孩儿死得安详,穿着华丽躺在椅子上,面带微笑。
伊萨克拍了两张,在近距离对焦于面孔时,女孩儿出神一般在相机取景框里嫣然一笑。
伊萨克即刻失了魂,疾速拍完,落荒而逃。
照片洗出来之后,伊萨克看到那张面部特写,那女孩儿竟又笑了。
伊萨克大骇,由此心神不宁,开始做诡异的梦,宛若天仙的安吉里卡从天上飞下来,抱着伊萨克在空中游荡。
奥利维拉以这故事与意象讨论了一个活人与一个幽灵的爱情。
这由心灵伪造的爱情极尽真实,却又极度幻灭。
就像影片中伊萨克在惊梦之后抽烟时领悟的那样。
影片画面中,香烟喷出后很快便消散开,“这是幻觉,却如此真实,就像烟一样。
”奥利维拉的画面风格一如既往地秉持着沉稳的艺术气息,所有的构图、人物站位、布光都按仿佛绘画一般一丝不苟。
这风格好似能将我们带往几十年前欧洲电影大师频出的年代。
借用《写意巴洛克》一书作者马慧元的一句话:“不是所有人都是时代的孩子,你永远不知道一个腐化的社会里埋藏着多么古典的精神。
”尽管这是写古典音乐的语句,但用在奥利维拉这曾经先锋,如今却古典极了的导演身上,恰如其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使用了大量肖邦钢琴奏鸣曲做配乐,且都由葡萄牙著名女钢琴家玛利亚-胡奥·皮尔斯(Maria-Joao Pires)演奏,这是影片画面之外又一不可错过的享受。
这两位艺术家已不是第一次合作,在奥利维拉1999年的影片《情归何处》(La Lettre)中,一个情节是一场小型钢琴独奏会,奥利维拉就真的请来玛利亚-胡奥,摄影机就端端正正拍摄了钢琴家的演奏。
■《安吉里卡奇遇》The Strange Case Of Angelica (2010) 国家: 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巴西导演:曼努埃尔·德·奥里维拉Manoel de Oliveira主演: 碧拉尔·洛佩兹·德·阿亚拉Pilar López de Ayala 、里卡多·特雷普卡Ricardo Trêpa等类型:剧情
3 ) 明月当空叫
大概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夏天住在姥爷家,姥爷讲过一个睡前故事,大意是这样的:从前有个老头,儿孙都已成家立业,自己住在住了一辈子的旧家里。
他还每天都要干活,虽然干的都已经是不挣钱的,自娱自乐的活。
但是他每天干完活,还要在院子里挖个坑埋点东西,邻居们看见了,都很好奇他在干什么,但谁也没看见过他在埋什么。
原来是因为,有天干活时,老头感到自己身体不行了,想让邻居把儿孙们叫来说说分家产的事。
但是当天夜里,却有陌生人向他托梦,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并让他不必把儿孙们喊来了。
于是第二天,老头告诉邻居不必把儿孙们喊来,并按照梦中人的主意开始行动。
行动其实很简单,老头在自家院子的树下挖了一个洞,每天都要挖出一些土来,过几天又会填上。
这样过了一些日子,所有的邻居都在讨论,老头经常在院子里埋什么东西。
这样又过了一些日子,老头的儿孙们先后回来看老头。
大儿子要接老头去养老院,二儿子要给老头请保姆,小儿子要给老头买电视机解闷。
但老头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三个儿子全都搬回来,每天和老头一起做饭,大儿子一起做早饭,二儿子一起做午饭,小儿子一起做晚饭。
三个儿子全都回来了,真的每天陪老头一起做三顿饭。
这样又过了一些日子,老头死掉了。
三个儿子争执一番后一起去院里挖,最后挖出了一个高压锅。
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这是个和阿凡提传奇或者西游记差不多时代的故事,但其实在姥爷的世界观里,它可能就发生在八九十年代,那是讲故事时的当下。
过了小半年,我让姥爷讲故事,他又跟我讲了这个故事几乎同样的版本,只不过院子里挖坑变成了老头他从房顶上拆下两块瓦当,在自己衣柜里腾出一口箱子,每天夜里睡觉前,都要打开箱子在里面折腾一番,这样过了一些日子,所有的邻居都在议论老头衣柜里藏了什么东西。
之后姥爷大概讲过三四个差不多的故事,也许更多不记得了,每次老头藏东西的方法都会有点不同。
姥爷的类型片之夏很快过去,另一个夏天我又去姥爷家住时,他又要讲老头藏宝系列故事,我就坚决不愿意再听了,因为从中根本不能听出什么寓意来。
“从前有个老头,他在院中劳作”。
二十年后我来到南方上学,这个故事偶或会被我自己梦到,于是场景又回到二十年前姥爷家的凉席上:每当夜幕降临,姥爷又开始讲述。
在度过了某种可堪忍受的无聊后,我就开始期待那个劳作不休的老头,这次要怎么藏他的奇怪的宝贝。
我一度以为姥爷潜意识中是在担心自己晚景的孤寂,但日常行事中的种种征兆显示,他显然已经超越了我这种浅鄙的思维。
那时的我根本不觉得姥爷这些千篇一律的故事是在糊弄幼稚的我,我唯一的感受就是,姥爷真是太神秘了。
看这种片只有一种感觉,就是以前的自己太土鳖了,以后还将继续土鳖下去。
如果没有经历过对上帝的信仰教育和怀疑,并不是就没有对归宿的思考和幻想,只是姥爷这种类似民科似的狡黠可爱,造就了一个对郭德纲古今传奇和奥利维拉cinematic情怀同时保持关注的我,种种混搭的土鳖审美,这才是我自己的安吉里卡奇遇。
4 ) 极度文艺的96分钟
拍摄手法很像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长时间沉默的留白,静景镜头,有着太多不可言说的意味。
配乐是钢琴演奏及纯人声民谣,整体在一种宁静与略感压抑的氛围下进行。
宁静,是男主人公的艺术素养所呈现的心境;压抑,则是他本人对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心理。
他眼中的世界上的美正在流逝、消亡。
美丽的年轻女子嘴角挂着微笑死去,为葡萄藤翻土的工人被机器取代,而房东太太的宠物鸟死去,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美不再存在,生命也就没有了意义。
于是,欣然随女孩的鬼魂离开了自己沉重的身体,去往他心中美的王国。
最后容我戏谑地说一句,给死人拍照的事最好不要做。
ta会把你带走。
5 ) 对过往电影技术的无比眷恋和怀缅
油画般的摄影,优雅的钢琴配乐,散发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古典韵味。
同样地,简练的人物动作和缓慢的电影节奏,令这部拍摄于21世纪的作品恍如时光倒流般,焕发出黑白默片的魅力。
这些都是大师奥利维拉的一贯风格,无需赘言。
我最感兴趣的是片中探讨传统/现代,物质/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隐约感到导演对过往电影技术的无比眷恋和怀缅。
不过百岁老导演丝毫没有与当下脱节的迂腐,餐桌上大谈欧洲经济危机的话题,现实意义不可忽视。
最惊喜是神秘主义的引入,莫名死去的小鸟和多次出现的老乞丐,都为这个现代聊斋故事增添一丝晦涩的宿命色彩。
6 ) 安吉里卡奇遇
恋物的极限[安赫利卡奇事]O Estranho Caso de Angelica导演:曼努埃尔·德·奥利维拉主演:利卡多·特雷帕/碧拉尔·洛佩兹·德·阿亚拉/利昂·希尔维亚/菲利佩 瓦尔加斯出品:法国Epicentre Films片长:97分钟媒体评论:奥利维拉可爱又悠闲地歌颂了浪漫,并在CGI的时代,制造了一出仿古的艺术品。
《华盛顿邮报》这是一出不可能的寓言。
《村声》既是爱情,又是恐怖,奥利维拉的电影不仅仅是有趣,幽默和极富野心的,它还有着更多的阐释空间。
《旧金山纪事报》奥利维拉的电影在给予我们视觉美感的同时,还捎带有关于人生和艺术的有力反思。
《看电影》 [安赫利卡奇事]是一幅古旧的油画,他不属于我们当下的时代,反倒更像是半个世纪前的作品。
他甚至比半个世纪的时间更久,因为他的内核,可以追溯到古老的艺术诞生之初。
这么说,虽然有些玄乎,但世界上最老的导演曼努埃尔·德·奥利维拉其长过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本就应该有着超脱凡人的不俗体验。
而观看本片的同时,也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快感,一种是对于单纯视觉美的欣赏,一种是和智者哲人通过作品的对话和思考。
在这个越来越爆米花化的今天,奥利维拉用这样的一部电影,回溯的其实是早已被时代抛弃的古典修养。
本片中,奥利维拉提出了一个极其值得思辨的命题,艺术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如此追随美丽,以及一个关于得不到爱情的宿命悲剧,短短90分钟的观影,向观众传达的,则是百岁老人对生活的执着以及对年轻爱情的眷恋。
其实,[安赫利卡奇事]已然超过了简单的恋爱,其将对美的崇拜,异化为恋物的讨论。
也许这份不计回报的爱,正是奥利维拉所追求的内心真实。
一幅油画的自我指涉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本片的视觉风格,那我一定会选择“如画一般”作为最终结论。
奥利维拉曾公开表示,如果不拍电影,他更愿意成为一名画家,事实上,在[安赫利卡奇事]中,他不仅仅做好了导演的本职,更展现了他极富经验的绘画构图。
闪耀的光线,毫无现代痕迹侵袭的乡间街道,以及基本处于静态,并没有太多走位的人物关系,都可以明显的看出奥利维拉电影和经典文艺复兴油画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
本片正如同大多数奥利维拉电影一样,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时代标志,看上去像是遥远的旧时代,但一些新款汽车的偶然入画或者人们讨论的实事话题,则又会让我们穿越到当下的生活。
确实,在[安赫利卡奇事]中,奥利维拉有意将时间背景抽离,营造了一种类型梦境的暧昧氛围,为影迷提供了一个可以躲避当下焦躁社会的途径。
不过,正如同[午夜巴黎]中所说的一样,每个人心中的黄金时代,都是别的时候。
而片中的男主角以撒,虽然生活在奥利维拉所梦想的旧日时光,却有着逃离现实的真切愿望。
而他所向往的则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只存在于幻想中的死后天地。
他渐渐的疏远了身边为柴米油盐烦心的普通人,被其照片中所拍摄的美丽少女安赫利卡的尸体所吸引,并且由于某些超自然原因,他看到画中的安赫利卡向他眨眼。
照片中她美貌脱俗,让以撒逐渐沉溺,并幻想其从照片中走出,带着他遨游太虚。
这样一个类似于《聊斋志异》的故事,放在不同的导演手中,则有着完全不同的呈现。
[午夜凶铃]中的女鬼走出电视,是对这类题材的保守拍法。
而前不久让影迷大呼坑爹的[画壁],则从猎奇的角度,展现了不同世界的一瞥。
但对于[安赫利卡奇事]来说,奥利维拉显然不需要这般的哗众取宠,他更想展现的,是一出有关美的寓言。
由奥利维拉本人的孙子利卡多·特雷帕饰演的以撒,有着与《圣经》中差点被父亲牺牲的无辜儿子一样的名字,他所代表的也正是奥利维拉被世俗牺牲的年轻纯洁的自己。
这位摄影师,热爱拍摄劳动者的照片,向往安赫利卡的圣洁之美,显然是一位理想中艺术家的形象。
但他经常拍摄的葡萄园劳动者,则让人联想其奥利维拉本人所拍摄的第一部默片[多罗河上的辛劳]。
在这部1931年的小短片中,奥利维拉初持摄影机,如片中的以撒一样,对于一切简单的事物充满好奇,这一层移情,明了异常。
同时,在不完美的现实世界,以撒的生活也是平乏的,导演巧妙的借用了几个侧面人物,展现了这层枯燥的无知。
在以撒所住公寓的大堂,奥利维拉巧妙的设计了一个下午茶聚会,在这里,人们讨论八卦,讨论股票,并且讨论以撒是个多么古怪的年轻人。
他们还试图将以撒拉入自己的下午茶阵营,但最终却被只在自己世界活着的以撒所忽略。
他只在意安赫利卡的笑容,如同奥利维拉只在乎电影一般。
最终,油画,少女和电影三者因为共同的美被导演巧妙的划上了等号,这也正是本片内在,最迷人之处。
一张照片的有力辩证 戈达尔曾经由词源学的角度有趣的辩证了照片,图画和电影间的内在联系,说白了其实很简单,毕竟在英语中,它们都叫“Picture”。
而在本片中,如果你换一个角度,理解片中复活的照片,则就会发现更美妙的影迷意境。
其实,整个电影的创意,在半个世纪以前的1952年,便已经有了雏形,那时候奥利维拉便构思了一个有关于照片复活的故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加工,和断断续续的剧本创作,终于在如今开花结果。
一个男人迷恋画(照片)中已死的女人,并且渴望咋现实中追寻其而去的故事,其实在影史上早已有范本存在,而其中最著名的,便要数希区柯克最富盛名的杰作[迷魂记]。
片中的金·诺瓦克在一开始所看的画像,正是詹姆斯·斯图尔特死亡迷恋的最初意象。
他幻想着画中数世纪以前的贵妇,爱上了眼前这位所谓贵妇的后代。
并在诺瓦克假死后,要求爱的女人,装扮成死者的样子。
这样由恋物发展而来的爱,其实便就是我们爱电影的真正原因。
虽然奥利维拉本人并没有明说,但[安赫利卡奇事]却替他说出了心中所想,我们爱电影,犹如以撒爱上照片一样,迷恋的其实是逝去的时光和永留在胶片中女人的影子。
正如齐泽克所说,“残疾的女人才是美丽的女人”。
而奥利维拉正是巧妙抓住了观众的恋物癖,将安赫利卡这一角色演绎成了美之绝唱。
想象一下,以个真正的女人会是如何的絮絮叨叨,可能她会像片中的房东太太一样,八卦不止,毫无美感,或者她会像安赫利卡家的管家一样冷言冷语,难以亲近。
事实上,除了死去的安赫利卡以外,全片中所有的女人,都没有丝毫让人爱怜之处。
似乎,只有经过艺术加工的商业照片(电影)才真正赋予了女人独特的一层蛊惑美丽。
观众爱的永远不是女人的真实,他们只在乎女人美丽的形象。
也许,这便就是在狗仔发达的今天,再没有嘉宝那般银幕女神的真正原因了吧。
毕竟,细节越被无限曝光的女人,越失去其神秘的美感。
我们越追求美好,便越会在现实中受挫,这也正是[安赫利卡奇事]片尾,以撒逃离人世,任魂魄飘走的内在解释。
现实中无法承受的丑与银幕上触手可及的美之间,以撒和奥利维拉,都选择了最理想主义的纯粹。
事实上,如果联系起奥利维拉之前的创作,便可看出其对纯粹美丽的追求,其上一部作品[金发奇女]中,男主角为了追求梦想中的美丽女子,开始跋山涉水,完善自己,甚至得不到理解与亲人决裂。
但当他满心欢喜,迎娶新娘的前夜,却发现未婚妻其实有着偷窃的毛病,追求完美主义的他,无法接受,只得取消婚约。
确实,要么追求绝伦的人世间至美,要么孤身一人,独善其身。
这正是奥利维拉电影中的男主角所奉行的人生信条。
而这近乎强迫症的怪癖,在[安赫利卡奇事]中则变成了毅然迎接死亡的决绝。
这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达到的境界,已104岁的奥利维拉,其旺盛的创作力,可能还离人之将死的状态尚远。
他的作品虽以死亡作结,但依然有着偏执的生命力贯彻其中。
所谓向死而生,正是对其心态的最佳定义。
这面对死亡的从容不迫,正有让人释然的力量。
如今,奥利维拉的新片也在紧张制作中,让人有了怀疑,也许忘我的工作,也是奥利维拉极致恋物的又一种表达。
★★★★文/西帕克(原载于《看电影》特别加映栏目)
7 ) 电影的气质
有时候翻翻自己的豆瓣,会发现诶我还看过这部电影?
怎么都不记得了。
或者原来给这部电影打了很低的分数哦,现在想想其实挺好看的。
这大概是艺术作品给到世界的馈赠,可以反复地被更新被认知被再解读。
就像第一次认识一个人,是我对这个人的认识不断地构建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其实这远远不会是他本来的形象。
第一次看一部电影,对电影的构建也就开始了。
这构建有很多层:第一印象,气质、环境、当时心情的好坏,自己对世界的认知,都是影响构建的因素。
第一次看《安杰里卡奇遇》,第一印象很特别。
我记得小时候看电影的途径很少,那时候貌似还没有电影频道,只有每周日的《正大综艺》结束之后,有一个《正大剧场》,那里看到许多国外的电影,印象很深刻的有《木头美人》《海底两万里》之类的。
说这个是因为这些电影有一些气质,我说不上这是复古的气质还是高贵的气质,总之很特别,是那个胶片年代,特效并不发达,电影还是一个神秘的行业时代的气质。
《安吉里卡奇遇》的身上就有这种气质。
想想这二十年,发展的速度是可怖的,无论技术上还是叙事上,无论电影还是这个世界,紧赶慢赶,着急忙慌,时代在飞奔,似乎自己还紧紧攥着时代的衣角,被拖拽着前行,有些吃力,有生怕被甩掉。
所以看万《安吉里卡奇遇》似乎很难忘记,很难忘记第一印象的平平无奇,很难忘记故事的简单潦草,想了又想,发现很难忘记的是这难得的气质。
导演是唐吉坷德,完全没有理会时代这个巨大的风车,单枪匹马,气盖山河。
电影真好,能抚人心。
8 ) [Film Review] The Strange Case of Angelica (2010) 6.2/10
Thanatological obsession comes aptly for a centenarian filmmaker-in-action (inconceivable but miracles happen), Portugal’s national treasure Manoel de Oliveira was 101 years young when he shot THE STRANGE CASE OF ANGELICA, his penultimate feature, he would pass away in 2015, aged 106.Set in an unspecified modern age (no cellphone or computer on show, the story goes that de Oliveira germinates the script almost six decades earlier, in the 1940s, which can well account for the film’s overall démodé tone), Sephardic photographer Isaac (Trêpa, a bland, even anemic leading man), lodging in a town near Porto, is hired to take some photographs of a young lady Angelica (de Ayala), who has just deceased and lies beatifically on her deathbed with an impeccable smile. Seen through his viewfinder, Angelica comes alive right in front of his eyes and smiles to him, even only for a split second, first startled, then bewitched (after A second visitation occurs after the photos are developed and hung on a line to dry), Isaac has an out-of-body experience with in his dream (de Oliveira and CGI technology make strange bedfellows). Henceforth, he becomes perversely retiring, glassy-eyed, refusing food intake (save the morning coffee), perpetually wallows in his own woolgathering and is deemed weird by the lodging’s other tenants and the over-hospitable landlady Justina (Teixeira), even his Luddite disposition (“old-fashioned ways interest me”), which de Oliveira initially makes heavy weather of, fizzles out while Isaac returns frequently to Angelica’s family. But what is he looking for, perchance even himself has no clue (all he gets is some glimpses of the family photo book). Exclaiming “Angelica” like a Cotard-inflicted walking dead, Isaac’s death-seeking, spirit-consummating wish never reaches an empathetic plane for audience to project our compassion, it is arrhythmic, unthinking and self-defeating. Having said that, THE STRANGE CASE…. is not entirely a misfire, de Oliveira still flourishes with his painterly instinct, divine compositions and chromatic understatement. Whether steeped in Chopin’s plinking virtuosity or basking in laborers’ collective, monotonous marching songs, we should only feel blessed and inspired by de Oliveira’s age-and-agism-defying quiddity, film is his Angelica and now they are finally and eternally indivisible in empyrean.referential entries: de Oliveira’s VOYAGE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1997, 7.0/10); João Pedro Rodrigues’ THE ORNITHOLOGIST (2016, 6.5/10).
9 ) 隔墙白影动,疑是玉人来
一名叫以撒的摄影师在下着雨的深夜接到一个富豪的电话,原来富豪家的小女儿安吉里卡过世了,他此次是被请去为小女儿拍遗照的。
小女儿身着一袭白纱,静静地躺在沙发上,脸上浮现着一缕祥和的微笑,睡着一般,仿若复古油画上的女子。
在拍摄的瞬间,摄影师晃了眼,他竟看见了姑娘向他眨眼的情形。
此后这个姑娘仿佛从摄影师的相片跑出来,摄影师常在半夜梦见她。
像是聊斋的故事,寂寞书生夜读,有女子从画中来,与之夜夜笙歌。
但想多了,这片子并不是一个恐怖惊悚片,也非奇幻爱情片,而是一部颇为沉闷的片子。
片子真的非常之沉闷,或许有所同感,才会找到属于它的轻盈。
简约的故事、缓慢的节奏、沉稳的色调、加上柔美的钢琴曲,有一种古典主义静默的艺术气质。
以撒刚出场时念着这样的诗歌,“舞动吧,星星,在令人眩晕的高度闪耀,你永恒地追寻、摇曳、升起,瞬息万变,逃离你被束缚的路线,时间在此静止。
而你,从前的人们啊,在幻想中穿行,于天国的路间漫步,天使们打开了天堂之门,因为我的黑夜即是白天……”诗歌是先声也是尾声,影片纯洁得像圣经故事。
和片子整体画风不符的就是照片里的这个女子不散的幽魂吧。
直到一夜,白衣姑娘安吉里卡飘然而至,带走以撒,两人如幽灵般绕过森林,飘过河流掬起水中的花朵,又像天边两颗星星一样尽览城市全貌。
天为被,地作床,两缕幽梦影,明灭可见,相拥而眠。
梦醒时分,他点燃一支烟,美梦亦如烟,让人迷醉,忽而易逝。
在梦里,以撒的身子是轻飘渺然的,而转向现实生活,他小心地避免自己陷入泥淖。
摄影师的身份是独特的,一只脚在尘土,一只脚在云端,他喜欢古旧的生活方式更喜欢用相机捕捉朴素的细节,他偏爱独居一室细细打量曝光成形的照片。
周边人多絮絮叨叨,他尤不爱发言说话。
自从飘来这一缕白衣幽魂,以撒开始躁动,直至从喉咙里、从灵魂深处发出声声“安吉里卡”。
身体有多沉重,梦里就有多缥缈,在梦里,安吉里卡在他的心田呵了一口气,以一身轻盈抵消他满身的沉重。
而世人只晓以撒得了失心疯。
葡萄牙著名导演曼努埃尔·德·奥利维拉拍摄此片时已是102岁高龄,历经默片、有声片、各国新浪潮,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和戛纳电影节的终身成就奖为他加冕过,到今天(前年去世)他仍守着自己的一方净土。
他的电影曾忠实于纪实,又转向致幻,《安吉里卡奇遇》无疑是两者的结合。
片子是这个世纪老人的自喻之作,尤爱古老事物的摄影师是他的化身,梦里的白衣女子是他对美的追寻,寻找的最后,失了魂,丢了魄,无望的尽头有了期待,这便是追寻美的极致了吧。
10 ) 复古的爱恋
奥利维拉在百岁之时拍出了如此浪漫,诡异,而又复古的作品。
油画般的画面,静默的表演,对逝去之物的爱恋在葡萄园里的工人和照片里安吉里卡的微笑中得以显现。
艾萨克在为安吉里卡的遗体拍摄照片时,美丽的安吉里卡在相机镜头里向他报以完美的微笑。
这是一个诡异的恐怖故事,但又如此妙不可言。
拍照是他的工作,相片是他的作品,如同电影之于导演一样。
安吉里卡就是艾萨克作品里的缪斯,如同安娜.卡里娜之于戈达尔,里诺尔.森威娜之于奥利维拉一样。
艾萨克爱上了这个完美的作品,同时,安吉里卡让他的作品变得完美。
艾萨克迷恋上了拍摄葡萄园里工作的工人,他忘我的拍摄这些原始的,挥洒汗水的一个个劳动者,随后将洗出的照片挂在房间里,一个个挥着锄头的男人与安睡的安吉里卡并排在一起。
艾萨克在睡梦中与安吉里卡拥抱着在空中遨游,飞遍天涯海角,他们如白色的幽灵般划过长空。
至此,艾萨克彻底的陷入了对安吉里卡的爱恋中无法自拔。
面对女房东在大厅里和朋友们以及其他房客关于各种八卦,现代科技,物理学理论的讨论,他漠不关心,他只一心念想着安吉里卡。
他在其他人眼中是个十足的怪人,异类,格格不入者。
他告诉女房东自己对现代科技和机械的反感,对人工劳作的痴迷。
他怀旧且质疑现代工具理性,他对逝去的年代和事物颇为痴迷,这似乎也是奥利维拉的心声。
每当他在梦里,在幻想中与安吉里卡相见时,总会被楼下的垃圾车发出的噪声打断,将他拉回现实。
这个时常出现的垃圾车声如此刺耳,这是现代科技特有的声音,是粉碎美梦的刽子手。
他看见女房东饲养的笼中之鸟死去后,疯狂的奔跑,大声高呼安吉里卡。
他似乎无法再忍受这个冰冷机械的世界,他要真正的和安吉里卡在一起,所以他死了,为幸福和那逝去的一切而死......他白色的灵魂跟随着安吉里卡再次从阳台上飞向天空。
他的遗体躺在昏暗的房间里的床上,房东为他盖上白色被单,放上十字架,关上唯一能看见阳光的阳台门,如同关上鸟笼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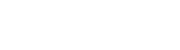
























越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往往就越是有趣,超越了本体的爱恋当然是存在的,也一定是更为高级的。有时候尽管阴阳两隔,但我爱你爱的发了疯,总想去你的国度寻找你,想要永久居留陪在你身边,却又终究受这副无用的躯壳所限制,使我不得开心颜。如果灵魂能够真正飞升,也许对我而言反而是种解脱,那时候我就可以义无反顾的去寻找你,去追寻我们之间爱的足迹,去构建更为美妙的千丝万缕般只关乎爱的联系。
这个导演是古典控
这才是真正的古典范,百岁大师的沉稳构图不是盖的
尽管影片意欲含晦地揭示物质、时空、记忆等系列命题间的关系,当仍被它造作的超现实手法所瑕掩。
差點導向男主角不眠狀態的反面。讓人無聊的是用這麼多說了這麼一點,還沒有使人感到言外之意。(3/5,2025-01-06)
时代、宗教、生死已经模糊。
摄影师给刚去世的美女拍遗照,莫名爱上了,最后灵魂脱壳死去跟美女灵魂走了。题材有趣新颖可以理解,但大量莫名停顿的画面,莫名的画面切换,莫名的无关紧要细节详细刻画,是为什么?肖邦配乐和一些噪音也不懂为什么,反而让人更没耐心看此片
7.6/人鬼情再续,没有相见恨晚。亚伯拉罕山谷原始的农耕方式和它的景致依旧协调,只是不知从哪儿来了个失意者,氤氲混沌,为爱而终。
《安吉里卡奇遇》人鬼恋:孤独的青年摄影师男主被大户人家邀请去给他们去世的女儿(刚结婚不久)女主拍遗像却被女主的鬼魂缠上,过程中男主为她的美所倾倒爱上了她与她谈恋爱,这也让他愈发与世界格格不入。不久后男主死去,他的鬼魂与女主的鬼魂终于终成眷属。
七夕观影浪漫主义似乎已死?
Si la Métamorphose est le cinéma
摄影师爱上死去女子的故事,由葡萄牙百岁导演拍摄。默片风格,节奏极缓慢,以肖邦钢琴曲作为背景音乐,气质古典隽永。以大量留白引发对爱情和生命的思考,如庄周梦蝶般,主人公倚爱之力,打破物我和生死的界限,放弃易幻灭的生命,走向极乐之境。
第一次看奥利维拉,构图和用光很考究,油画感十足;导演清楚地展示了拍摄电影的代价:摄影术即摄魂术/招魂术,将已逝的不在场的美定格为永恒的在场,势必招致幽灵的回归——而他却轻描淡写道:我仅是想留住旧日之美;同为潜在的元电影,结尾的处理(驻足于画框)和阿巴斯的如沐爱河相仿,关上门窗颇有辞别之意
“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只不过是单相思而死,像是上世纪的鬼片,拍片时导演都102岁了!敬业!
现代影像和古典情怀在奥利维拉轻盈又unheimlich的《安吉里卡奇遇》里令人惊艳地嫁接在了一起。这位百岁导演是在轻轻地追问影像的本体性。于是摄像机承载了死与生之间的摆渡船:它可以把死去的女子复活,也可以把劳作着的工人变成幽灵(马克思的宣言还飘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梅里爱的技术在21世纪的数字画面里鬼魂般游荡,这种不确定性让人无法从语义上“理解”电影,只能纯粹地体验影片宁静又流动的视听元素。
果然是百岁导演才拍得出来的作品,古典老派且纯粹归真。劳作的农民和已逝的佳人相片悬于房下,有生的沉稳,也有灵的轻盈,死亡并不苦痛或惊悚,是服从心向往之的召唤。为一丝不苟的油画设景光影构图叹服,漂浮在湖面上梦幻如夏加尔,我需要一双眼睛学着欣赏这种审美。
人鬼情未了,之后就鬼鬼奔天涯了。男人魔杖不浅啊
4.5。当摄像机的快门被按下的一瞬,一个画面就此定格,可这便是影像的全部吗?——它们会在想象的世界里自由地绵延,就如相片中挥舞至半空的镰刀会继续落地一样,笑容的永恒也超越了生命与死亡的界定。看奥利维拉的这部电影,像走进一张张油画,走进这些画面绵延而成的世界;静态的情境缓缓洇开层层涟漪,这是宁静的时间与空间和它们容纳的一切为情绪、视线与话语所牵动的难以言喻的古典之美。
有个人早睡早起,后来他死了。五毛钱特效用得稍微再节制点,也好一些。
古典主义&印象主义,百岁导演的遗作之一,老导演的世界观和对于人生的看法,诸如生死、爱情、现代与传统。也许只有死去的东西(过去的东西)才是最美的,才是永恒的,那就活回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