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梦之家》剧情介绍
本片是斯皮尔伯格受成长经历启发的初心之作,讲述了主人公萨姆·法贝尔曼(加布里埃尔·拉贝尔 饰)的成长经历。萨姆从小就爱上了电影,并尝试创作属于自己的电影。这一兴趣得到了他的艺术家母亲米兹(米歇尔·威廉姆斯 饰)、计算机工程师父亲伯特(保罗·达诺 饰)以及家中其他人的一致支持。如果说电影是造梦的艺术,那么法贝尔曼一家就是一个“造梦之家”。 多年之后,萨姆已成长为一个天才的少年导演,凭热爱创作出一部部令人惊喜的业余电影。但意外的是,通过摄影机的镜头,他发现了一个关于母亲的心碎真相。而这将改变他与整个家庭的未来。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致命玩笑雨天遇见狸黑暗漫步摩耳摩东岸线约翰·多诺万的死与生编剧情缘我们的四十年热血高校2彩虹时分庙街妈兄弟哈卡无敌县令红旗渠的儿女们大降魔师家有喜旺第二季隨懿深度行盗墓迷城两个世界之间曲面吸血鬼侦探重生小确幸爱慕塞上风云记玻璃谜城梦想至暗之时孝子罪恶之家绝世好宾
《造梦之家》长篇影评
1 ) The Fabelmans
2023-05-28 19:15颇真诚,尽管仍不失名导商业手笔,仍能以从业多年的人生体悟,将才华艺术家的挣扎内心和五味杂陈人生娓娓道来,勾勒出从艺者复杂又动人的一生肖像(想起东木头的“忏悔”,也给自己开脱?
)。
人物必然出彩,Williams贡献出色演技(而且为什么这样的角色第一感觉“就是她”),然而仍有小bug。
庆幸故事中角色最终都看清了自己和家人的关系,作了自己的选择,还有家人间的互相理解和互相支持。
一家人艰难抉择的过程作为故事着墨的重点难点,叙事清晰表现到位选角得当,没什么遗憾了;甚至还有怪舅“艺术和家人将撕开你”的一句话挑明(主要矛盾),既照顾了大众理解又保持了自然不觉生硬。
至于是什么让人下得了决心作得了决定,也用言语表明了——正是家人对你的深刻理解和支持:“最终都会拼尽全力”,对后来才华者也有具体的参考意义。
Dano做到了角色需要的,然而此角对他本我来说有点憋屈?
欣赏好莱坞级怀旧片的调研功夫简直是享受,装潢、历史时事、衣着品味、器材、各州人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少年小时像猫王,少年像美队。
配乐大亮点。
关于拍电影,幕后揭秘(抖包袱)也见主创情怀:胶片机经典型号、剪辑核心(胶片剪辑)、动脑(造梦/模拟效果)、说戏总关情(煽动性然而能走进内心=感染传播)、叙事的上帝之手……故事中少年恐惧,却以求证的态度处理,注定杰出;母亲“事出必有因”的信仰也如出一辙,看似小习惯却影响重大。
结尾颇意味深长(并且再次运用了导演“上帝之手”的权力):Life is not a movie,但光为造梦仍然造出了一座城,有自己的牛B办公室(完全你自己的规则话事)……带别人一起发梦……
2 ) 电影,两极化的私密之梦
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造梦之家》里,斯皮尔伯格几乎对自己一贯被认知的电影内核,进行了一次推翻和重读。
他往往被认为是“造梦者”,而这也正是电影本身的定义。
然而,在这部作品中,斯皮尔伯格告诉大众,电影是“梦”,以创作者的个人情感与内心世界的表现为核心。
但它却未必永远是美妙的梦,反映的是人的各种梦境,更包括了童年时代经常会出现的噩梦。
而基于梦对人内心情感的反馈功能,电影就成为了创作者将所感进行具象化的存在,而这往往是不分“积极或消极”的。
电影的开头,我们就看到了斯皮尔伯格对“不美好的梦”与电影的关联建立。
男主角患有焦虑症,而他看到的电影画面并非父母口中的“美梦”,而是火车撞死人物的灾难场景,他的表情透露了他极度的惊吓。
然而,这并没有打消他对电影的兴趣,反而一次又一次地用玩具火车与微型摄像机,重现着惨剧的一幕。
显然,就像他看着让人压抑的滤波线条而回想起电影画面一样,拍摄的内容成为了他负面情绪的延续,而他却沉浸于此,因为这是对他这一情绪的无限放大。
在拍摄一系列画面的串联剪辑中,男主角对负面情绪的热衷也显露无疑。
他拍摄拔牙,拍摄突然冲出的骷髅,在校期间拍摄的殴打他的校霸,拍摄西部牛仔对女孩的劫持,拍摄牛仔决斗后的死亡。
这一系列的题材,或来自于他自身的疼痛记忆,或来自于他看到的电影,无一例外都与他感受到的负面情绪有关,特别是以仰拍的方式制造逆光角度,特写强化牛仔的尸体,完全将负面情绪放大了。
而出现在他手上,被捧在掌心宛若珍宝的,正是这样的画面, 不够美妙,但却具有着梦境一般的迷幻感。
显然,斯皮尔伯格强调,创作电影之“梦”的来源,在于创作者从个人经历中的感受性,而这种感受性并非完全积极倾向,创作者本人的人生也未必十分美好,但这都会酿造出消极但优秀的作品。
电影的梦境,便是创作者的情感载体,这也是各种艺术创作的共同特点。
男主角的家庭,构成了这样表达的主要载体。
男主角的父母并不和谐,母亲是“电影之梦”的引路人,给儿子买了摄像机,而她自己也是钢琴家出身,热爱跳舞,亳不压抑自己的情感表达,艺术化倾向明显。
相对地,在现实层面,母亲对于烹饪等生活杂务则完全不拿手。
而父亲则是相对的现实者,他从事计算机的理工工作,与艺术感性的妻子不对路子,其母也在意儿子的社会地位,对不习惯烹饪等主妇生活技能的儿媳妇不假辞色,打断她的说话,也鄙夷地看着她烤坏食物。
在第一场戏的阐述电影时,父母交相说话,差异显而易见。
父亲解释着电影的物理学原理,以及拍摄对象“玩具火车”的运动原理,而母亲则只是用“进入梦境”等重体验的感性短句。
而在协助主角拍摄西部电影时,父亲也要一边扇风一边应付着车主,显然是片场众人里唯一不在“梦境状态”里的一个。
而母亲,则会在对抗着餐桌上吵嘴的时候,背着“一片狼藉的残羹餐盘”特写所强化的凌乱现实生活,偷偷给儿子一盘放映带。
她是感性而艺术的,与现实理性的丈夫存在着先天的割裂,并对同样自我的丈夫同事心有好感,从而带出了男主角痛苦情绪的重要来由:离婚。
以一般逻辑而言,母亲代表了电影的“梦境”,也确实是男主角创作的引领者,而父亲则是电影作为“梦境”的否定者,将它拨回到了光学原理的理性层面。
母亲的离开,似乎意味着男主角创作生涯的结束 。
但不这样做,恰恰是斯皮尔伯格的高明之处。
事实上,男主角居住在这个父母割裂的家庭中,这便带来了他在感情上的苦痛,但这种苦痛本身也化作了他的创作内容。
在电影中将一切情感---必须深切,但无需正面画面化,传达给观众,才是男主角的创作推进能源。
最典型的一幕是,男主角发现了母亲的外遇,但只是将之拍下,并没有告知父亲。
这是有趣的设计思路,一方面,它说明了男主角在电影“梦”呈现倾向上的非绝对积极面,另一方面,也让“创作”之于外部审视准则的“正确性”被弱化了。
这样的弱化,在父亲并非冷血莽汉,反而愿意支持儿子之上,得到了对其必要性的确凿:情感无绝对好坏之分那么简单,而电影创作也不能以既定观念而作为标准,评断作品是否具有水平。
另一方面,斯皮尔伯格还赋予了父母以更丰富的隐喻内容,即对“电影”的象征。
在第一场戏中,将电影表述为光学技术的父亲,以及将之称为“美妙的梦境“的母亲,已然完成了各自承载的“电影”侧面的象征意义,并将之同时灌输给了站在二人中间的男主角。
可以说,父亲与母亲的结合,才是“电影”的完整样貌,既是技术也是“感受”。
而结合的破坏,反而让男主角的极度的负能量下,拍出了足够浓烈的作品。
这带来了一层对电影的隐喻:外物的技术,私密的艺术,二者并立,方才组成了完整的电影创作环节。
父亲象征前者,其初衷并非恶意,对应着后续主角在行业中受到的待遇,而它的存在本身是为了影片的受众面与利润考虑,是成本较高的电影行业能够维持下去的必然要求。
更具体地说,斯皮尔伯格甚至强化了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受害”感,让他在妻子与部下的“和谐亲密“面前感到尴尬,在融入对方的整个家庭中被排斥。
最为典型的,便是他在亚利桑那的篝火露营上的表现---先是与众人温柔地合唱,显示出自己全力维持家庭的正面状态,而后部下突然开始更激情且放荡地高唱,吸引全部家庭成员的加入,而他则只能尴尬呆坐,并在随后看到了妻子对自己”离开亚利桑那”的逆反,反而支持本尼的“留下”。
如此一来,电影就避免了父亲作为“电影人男主角的阻碍者”所易于落入的负面观感,也就此强调了电影技术面的重要性,没有技术的发展就不会有电影的存在与后续逐渐升级的“造梦”手段。
而母亲象征后者,同样被淡化了负面感。
同样的露营段落,在父亲进入“被同情”状态后,斯皮尔伯格迅速地让母亲“扳回一城”,在汽车的灯光前翩翩起舞,而与她存在私情,最容易引起恶感的部下本尼,也通过“打开车灯,创造男主角拍摄条件”的方式,建立了自己与电影的正面关系,这显然是代表着“重视个人内心体验的艺术”。
此时,因母亲与部下出轨,以及其在男主角镜头中留下暧昧画面的永恒存在,成为男主角在创作与人生中不可消除的不美好痕迹,并带来他随后的单亲家庭体验与父子的分裂,“电影之梦”淡化了其对普世标准的吻合性,成为了对电影之绝对个人私密情感化的艺术侧面的写照。
在电影的第一阶段,斯皮尔伯格承认了电影在技术与艺术之间的二重性。
作品开头,斯皮尔伯格将技术感十足的”滤波器“与代表“负面记忆”的电影声音并列,共同作用于男主角的视觉与听觉,形成其对观看电影的感受,已然说明了这一点。
技术的研发促进了电影表现手段的发展,而这才是导演们的可运用工具愈发丰富,执行更多的奇思妙想,从而实现自己的“造梦”并表达自我的关键基础。
在电影里,斯皮尔伯格反复强调着父亲对技术的痴迷,给了他很多“解说技术”的桥段。
这看似是闲笔,实则强化了父亲对技术痴迷的正面形象,从而以其象征意义,引导出了电影创作中技术的重要性。
并且,电影也建立了父亲与男主角的某种共性。
例如,在二人开车的两个段落中,先是儿子对解说电脑技术的父亲说“慢点开”,随后画面迅速切入下一场戏,二人在车内换位,父亲对解说电影特效技术的儿子说出了同样的台词。
如此一来,重视技术的二人的共性就此达成了。
以其父子关系并不融洽的状态而言,斯皮尔伯格似乎抒发了自己对于技术的感受:承认其重要性,但也经常因其所限而备感苦恼。
与此同时,斯皮尔伯格也当然更加强调了决定其创作水平的“情感表达的艺术”一边,让男主角最终倾倒到了父亲的反面。
电影的价值,在于它的情感是否强烈,而对其的审判与定性则是不重要的。
而对于“梦境”内容的”非纯粹美妙”,电影里也有着丰富的细部表现。
在露营的结尾,母亲跳着被拍摄下来的梦幻之舞,让电影之梦的美妙达到了一个小高潮。
然而迅速到来的,便是父亲注视着的心跳显示器,是男主角外婆的重病。
心率的频线,让人联想到了开头部分里男主角凝望的滤波显示器,共同构成了男主角的不美好感受,而却又与”电影“产生了关联-开头时,男主角直接回想到了在电影院里看到的火车事故画面,而在这里,男主角则凝望着奶奶的脖颈,对其产生了如电影拉近镜头一般的深度观察与感受。
而当奶奶去世后,代表”艺术“的母亲,也摆脱了之前的纯粹美好状态,愈发地被亲人离去的黑暗记忆所影响。
特别是影响开启的瞬间,她从梦中惊醒,以其”噩梦“状态而直接对应了电影的”造梦“,进一步说明了”梦“与私人情感的复杂。
随着夫妻关系的走向破裂,二重性的表达也进一步延伸,成为了“技术”辐射出的“现实”与”艺术“之"内心表达“的关系表述。
事实上,借由纯粹技术设备的“滤波器”到宣示外婆死亡的“心率监测仪”,含义的延伸已然完成,“现实”的内容从技术层面上升,与男主角的感受与情绪有了更直接的关联。
生活里的阴暗要素无法摆明,更谈不上开解,于是在隐忍中形成了巨大的痛苦,只能以电影的形式宣泄出来,成为了内心表达的出口,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成为了创作欲望的驱力。
由这种负面情绪而生成的“以作品表达”的宣泄需要,这二者共同组成了作为电影人的男主角的生活,也带来了电影创作的“造梦”之不美妙。
“造梦”的“家庭”本身的不美好,成为了对此的十足象征。
它当然带给了男主角以痛苦,有着父母的离婚,以及自己不得不在面对父亲时闭口不言母亲出轨的难堪。
然而,也正是这样在内里已然分崩离析的家庭,才造就了男主角的“电影之梦”,成为了他表达的“梦境内容”。
首先,是男主角伯伯的到访,他给出了对此的第一个表达。
他来自好莱坞,告诉男主角要在电影中感受“现实与艺术撕裂的痛苦”,这也正是对男主角不完美家庭的描述:“现实”的父亲与“艺术”的母亲,结合在一起,生成上述的痛苦,并以痛苦去推动创作。
这样的割裂,是男主角作为电影人的状况,也是他创作电影的源泉---一种对现实遭遇进行反应的,非绝对美妙正面的情感表现,一场不一定甜蜜的复杂之梦。
在随后的发展中,我们也能看到男主角的相应体现---在内心感受上,倾向于与母亲的艺术共通,有着二人之间的深度共情,但站在现实角度上,他却无法接受母亲因“艺术化的自由之情”而出轨的背叛父亲行为,无法完全消化艺术在现实生活里的冲突,也不能将之当作理所当然。
放映军事电影时,他在电影院里与母亲共情,结束后却无视母亲而走向父亲,即表现了他的自我割裂之痛。
而这种痛苦的情绪,以及作为反馈而出现的“心灵缺口的弥补”,便是电影创作的核心诉求和内容构成。
而伯伯自身带有的肮脏与无礼,也正是对“电影“完美形象的打破。
并且,斯皮尔伯格也让他叙述了电影造梦基地好莱坞的”种族化“现实,说着在当代视角下带有黑人歧视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以及行业里的犹太话题,提示了”梦之源头“并非纯粹的美妙天堂,而是混合了很多现实因素的负面事实,暗示着电影中蕴含情绪的“对现实非正面反馈”属性。
他坐在桌边描述着电影,与此前认可女儿钢琴造诣的外婆同样的不完美形象,淡化了钢琴与电影的完美感---高度类似,而旁边则是收拾餐桌这一现实感十足的动作,构成了对艺术与现实严重分化对立的暗示画面。
这样一个家庭画面,与几乎每一个家庭全员出席的全景镜头一样,都带有强烈的“不完美”感,或直接给出肮脏邋遢的氛围,或潜藏有出轨的暗流,正是对此间家庭所造之梦的属性表现:它带来的情绪反馈之梦,必然不会是完全积极的。
而后,”电影“的二重性,开始以非常明示的手法得以呈现。
在男主角播放露营影片的时候,母亲弹琴与父亲手拿绘图铅笔的镜头,始终以独立的状态分别穿插其中。
这让电影同时具有了二人姿态带有的两种属性,而父母各自的晦暗表情,以及父亲对琴声接收时的勉强为之与无法进入,也说明了二人此刻已然分道扬镳的夫妻关系,构成了二重性带来的痛苦,并进一步引导到了影片的画面之上:母亲出轨的关键瞬间。
首先,这将带来母亲的离去,使男主角失去最支持也最理解其电影追求的人。
然而,当画面切换到下一幕,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痛苦对男主角创作的加成:他用战争场面的鲜血与死亡来表现自己的情绪,用等同于家人的士兵的覆没来对比自己家庭的分裂,用长官"因自己无能而使得家庭死亡”的痛苦来宣泄自己的痛苦。
而在这里,“现实”与“艺术”的并立也再次得以呈现在电影放映的艺术环境之下,母亲与男主角形成了流泪的共鸣,而当影片结束,回到现实中的男主角则会拒绝母亲的问候。
电影作为不完美现实的情绪表达出口的作用,在此得到了明示。
在电影中,每一次的”搬家“,均对应着家族走向新一层级的现实毁灭,也带来现实与艺术关系的探讨升级。
在搬到加州的部分中,斯皮尔伯格将“现实与艺术“的探讨带到了更深度的中心区域。
他让男主角试图从电影走到现实中,在后者的环境中更积极地表现自我,解决问题,因为电影终究只是虚构的世界,无法更深刻地影响现实生活。
而这种努力的失败,也恰恰构成了电影中由负面情绪所组成的”阴暗之梦“的来源。
可以看到,电影中呈现的内容与情绪,始终是偏向负面的,是男主角在现实中不可言说,必须压抑的无法面对之情。
这样的表达渠道对男主角格外重要,但却也无法接入他的现实生活。
如此一来,“艺术与现实的痛苦”,便完成了升级。
男主角无法改变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困境,由此产生的情绪必然是不全然美好的,而他能做的只有在电影中消化这些情绪,或直接宣泄,或自我安慰,是他“复杂之梦“的展现载体。
此前拍到母亲起舞而父亲无措,另一边却是母亲与本尼眉目传情的家庭现状作品,以及那部暗喻家庭分裂而自己无力的虚构战争电影,以及随后会出现的直接捕捉母亲被父亲拥抱时尴尬表情的家庭纪录片,因自己身体瘦弱而聚焦校霸的健美强壮以示艳羡的学校电影,都是如此。
在搬到加州前的战争电影放映会上,我们就能看到男主角的这种状态在放映时,他与母亲与本尼形成深度的情感联结,但当走出放映场所,他却只能留在父亲的身边,对母亲和本尼的不伦之恋只能通过电影的形式进行”接受“,在现实中则只能远观,甚至无法对母亲直接说出自己知道的真相,取得解决问题必要的第一步沟通。
接下来的一幕,是对这一点的最佳诠释。
他背诵着救生员的守则,却被母亲用轻佻的玩笑惹怒,显示出二人在关乎生死的现实大事上的态度分裂,而现实中的无法共通,也旋即直接体现在了母亲的出轨一事上--二人激烈争吵,几乎让男主角脱口说出了自己的知情,但他最终却只是愤然离开了房间,被母亲狠狠地拍打在后背上,机会瞬间消失。
而更加有趣的是,斯皮尔伯格随后展示了”电影“的层面。
男主角走向自己房间的走廊画面,伴随着光线从现实感较强的自然光氛围向卧室中整体黑暗、后置一个焦点光源的朦胧”电影远”氛围的转变,而在这个氛围中,男主角才与母亲取得了情感的交换,通过沉默地播放电影中不伦画面的方式。
然而,男主角无法将实情摆上桌面,只能与母亲达成隐秘的心照不宣,这就让他们对问题只能停留在“掩盖”的程度上,而远远无法解决。
就像他说的那样,“我不会告诉父亲的”,对代表现实的父亲隐瞒真相,就意味着婚姻关系永远是个麻烦。
他在电影里所展现的一切情绪,无论是家庭的分崩离析,还是母亲与本尼的出轨,也就得不到扭转。
电影中能够作为画面的,只是如他对加州学校里的校霸所说-“摄像机所能看到的画面”,是对自己观察之物的反映,而不是“对其进行解决后的改良状态”。
在随后的部分中,斯皮尔伯格展示了男主角和母亲对此的一系列改变尝试,以及最终的失败。
男主角试图回避电影中记录的阴暗真实,甚至干脆卖掉了摄像机,希望与母亲一起面对现实,在生活中逐渐消化它,解决危险的夫妻关系。
在二人听到父亲“殴打本尼的梦”时,已然做了"我以后只会是你的妈妈“的约定。
而在另一方面,男主角在学校中遇到了校霸的欺凌,其原因是伯伯提到过的”人种”问题瘦弱的体型让他在体育课上被欺负,而犹太人的身份则导致了“几乎没有犹太人“的加州对他发自于信仰的排斥,”为了你杀死的耶稣而道歉“。
作为对此的开解,男主角遇到了心仪的女孩,几乎解决了他在现实层面的种种问题。
她的情感外露,与现实里内敛隐忍的他形成互补,推动着他抒发出自己的情绪,二人在耶稣十字架之下的拥吻,不仅意味着男主角被耶稣的“谅解”,人种与血统隔阂的解决,更代表了女孩对于他“现实层面之救赎”的意义。
这甚至延伸到了男主角的家庭问题上:在女孩参加的聚餐段落中,父亲一开始喂食母亲的猴子,似乎非常和谐,但二人对男主角拍摄电影的观点随即分化为“玩闹”与“支持”,并在全景中分列两侧,尽显对峙姿态,就像每次聚餐中必然存在的割裂感一样,而帮助众人从这种尴尬的沉默中挣脱出来的,正是继续谈笑自如的女孩。
但是,发生在现实层面的积极因素,最终还是消解了。
母亲虽然试图让婚姻进行下去,但她与丈夫的思想割裂终究不可解决,埋在二人心中的“出轨”更是成为了一根致命的刺,随时激发着不满,却又由于母亲的回避而无法坦白曝光。
在男主角与父亲激烈争吵的段落中,他将自己由于人种而被孤立的痛苦摆了出来,也用“你只是在逃避本尼”的言辞几乎逼迫着父亲直面出轨的事实,这是他对“改变现实”做出的最大努力。
然而,母亲却在此时站到了沙发上,用一种完全回避的态度使得父子二人重归沉默,浪费了离婚之前的最后一次解决机会。
随后,男主角延续了对此事的沉默,不再在现实中发表任何意见与情感,而是将一切都留在了电影中。
当女孩们痛斥着母亲时,他只是坐在了女孩们的“反打镜头”中,甚至一度与后者出现了“镜中与非镜中”的区分,始终不发一言,单纯地在一个背后视角中观察着这一切。
而”情感“则发生在了”电影“的层面他剪辑片子,与妹妹一起观看,才解除了此前基于”镜中画面“的分裂关系,相拥在一起安慰彼此,形成了基于痛苦情感的共鸣。
这也体现在了他和女孩的恋爱中,当他在舞会中说出了自己的家庭问题时,迎来的却是女孩的愤怒与离开,二人的关系始终以“电影”为连结---先是沙滩活动中对着摄像机的亲切互动,随后是离开后的女孩看完电影,又重新试图与他交谈。
甚至,面对着校霸,男主角也要用电影来做出一些表达用镜头抒发对他健壮与阳刚的羡慕,随之方才带来了二人在现实里的一些真实交流。
由于现实中的无为与沉默,任何问题都无法被解决。
男主角只能对既定的问题进行观察,随之感受到情绪,并将这种情绪承载到电影里。
他在“先天”问题上被排斥,因为瘦小和血统而被殴打与责备,于是将对强壮身体的羡慕反映到对校霸的聚焦之上。
这让他与校霸有了交流,二人的关系却也停留在此。
他通过电影似乎重新唤醒了女孩对他的沟通欲望,但这显然无助于女孩的离开决定,“分手不一定在舞会上,但一定会的”。
最为典型的,则是他拍摄乔迁画面里的父母---父亲亲吻并拥抱了母亲,然而母亲的微笑却显得勉强,让这一幕从“母亲努力的实现,夫妻问题的解决”变成了“表面和谐内里分裂,夫妻问题的现状”。
现实里对家庭破裂的无为,在最后一个阶段中达到了巅峰。
母亲与男主角站在厨房中谈论着曾经的动手,试图消解在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但最终却依然落到了“我无法离开本尼”的不可调和。
此时,“做饭”的意象也最后一次出现,成为了母亲做糊了的鸡蛋。
在电影里,“饭菜”反复出现,在每一次家庭聚餐的段落里呈现出凌乱的状态,或是“不好吃的菜肴”,更多的则是“被收拾掉的杂乱剩菜”。
这种家庭齐聚的聚餐变成如此状态,无疑是对男主角所处家庭关系破裂的暗示,也由当时母亲与父亲分立艺术与现实两端的矛盾而说明了原因。
而到了这最后一次,鸡蛋被完全做坏,母亲也彻底离去,甚至连餐桌边的都只剩下了母子二人。
这构成了男主角在现实里无法挽回家庭的痛苦,而他与母亲的共情,也依然只能在“艺术”中发生。
此刻,二人相拥而泣,镜头推拉到空无一人的餐桌,光线的明暗完全将两个空间割裂开来---男主角在艺术层面与母亲的共情,显然无法作用于现实层面,因此他也只能获得哭泣的负面情绪。
而在另一边,我们也看到了男主角对于父亲现实生活里的无能为力。
当他因为母亲一般的敏感情绪---偏向艺术感受一面的---而呕吐时,父亲所做的只有特写镜头里的“沏茶”,将之称为现实角度出发的“紧张症”解读,二人的分裂已然体现。
随后,父亲看到母亲与本尼的照片,背后的墙上映射出黑色的人影,仿佛将他分成两半,无疑也暗示了他落在现实中的本体与母亲生活的远离,能够靠近的只有虚幻的影子。
而对于儿子收到电影公司邀约的信件,父亲也只是尴尬地说了一句“好消息?
”现实里,人面对着太多的困难,让电影成为了对现状的情绪出口。
这是电影的功能,也是电影的局限,它能反映与宣泄人们的“内心反馈之梦”,但并不能让“梦”照进现实,改变更多的生活困境。
男主角试图抛开电影,掩盖那些黑暗的情绪,但他在现实里无为,发现自己只能回到电影里,否则便失去了哪怕“表达情绪”的平台。
在他卖掉摄像机时,与本尼的交流便已经暗示了随后在加州发生的一切---他拒绝本尼的送礼,也卖掉摄像机,但最终却依然接下了对方给的新摄像机。
而在加州,当母亲阻断了他与父亲吵架的难得坦诚机会,他丧失了最后一次解决家庭矛盾的机会后,躺在床上触摸摄像机的画面,让电影重新回到了他“宣泄现实中阴暗之梦”的地位。
“现实与艺术会撕裂你”,并不仅仅是二者的对立,更延伸成了“现实中无能为力的痛苦,成为艺术表达的对象,让导演宣泄以创作的动力,却也让导演不得不直视它”的含义。
这也就让我们理解了斯皮尔伯格相应题材的很多作品,如《et》里孤独外星小孩获得的家庭温暖,如《人工智能》里重新找回母爱的ai男孩这是一时的美好,但却无用于电影外的现实生活,在电影里也要落回到外星小孩的离开,ai男孩的死亡。
斯皮尔伯格造出了瞬间的完美之梦,这是他对自己现实人生的些许慰藉之情,但其情最终会回归成对现实的既定反馈上,变成瞬间慰藉后的长久遗憾,电影营造梦境的余韵也不再那么美好。
作品的结尾,是斯皮尔伯格对“电影”本身的一次直接呈现。
与父母在不同层面上产生了巨大分裂,受困于艺术与现实割裂之痛,生活已然不可调和的男主角,走入了电影的圣殿,接触到了电影的本质。
当他坐在约翰福特的办公室里环顾四周,所看到的是一幅幅的电影海报,这一切笼罩在仿佛由放映机投射而出的光晕之中,构成了电影的美妙之梦。
然而,这种美梦被迅速地打破,先是约翰福特冲进门时的噪音,随后是他手上的鲜血,并最终落实在了他对男主角极其粗暴的态度之上。
电影世界的梦,由此而变得“黑暗”了起来。
但是,最关键的一幕,发生在了福特对电影海报的解读之上,构成男主角身处电影世界的海报,也就此实现了对这一世界的定义。
在福特的逼问下,男主角解释着海报里的内容,用非常现实的视角描述其中的细节要素。
然而,福特却两次打断了男主角,告诉他“地平线位置”的重要性“地平线在顶部,很有趣,在底部,很有趣,在中间,不有趣”。
这是微妙的解释,它去除了海报里一切具体事物的存在意义,转而突出了构图对海报观看者的感受引导作用:地平线在下方,观者可以顺着人物的远眺目光看到深景里的远处,反之则可以看到发自深景处的纵深,留出的构图中间区域成为了纵深“绵延”感的强化,不制造任何遮挡,皆是对于空间之广阔,以及其间人物心境的感受,进而引导出约翰福特的西部电影里标志性的粗犷、原始、奔放等情绪。
同时,非顶即底的“极端化”,也是对于男主角的提醒:接受并反映快乐与黑暗的两极情感,引导对内心极致形态的感受性,这正是电影的魅力,也是此段中的约翰福特自己,及其电影中那股浓烈质感的由来。
由此一来,约翰福特对电影海报的解释,无疑成为了对电影本身的说明:最重要的不是其中的任何具体细节,而是情感,与情感密切相关的创作者内心的抒发与表现,是对它的创造、输出,并引导感受。
这样的情感并不发生在现实里,而是办公室象征的完全独立的电影内部世界,因此无法改变现实里可能存在的负面痛苦,只能作为对其的反映出口。
约翰福特本人在此段中的气质,其扮演者大卫林奇在《妖夜慌踪》《双峰》《蓝丝绒》《穆赫兰道》等名作里呈现出的一系列“通向人物心灵负面深处的暗黑之梦”,都是对如此电影之梦的属性表现。
而在最后一个镜头里,我们也看到了男主角的终极出路。
他接受了约翰福特告诉自己的一切,终于欢乐地站到了电影片场林立的过道之中。
显然,他依然无法解决片场外面所发生的一切,但他知道,通过电影创作,他可以表达自己的全部情感,让电影成为自己梦境的出口,承载起现实世界里的不可言说之痛与不可承受之重---或是以直接的自白,或是以暂时的抚慰。
他只能做到这一点,而他也终于接受,并在这条路上前行下去。
显然,斯皮尔伯格完成了对自己电影生涯的一种细化陈述,先是对“技术与艺术”的观点阐释,而后升级到了对自身创作观与电影认知的剖析说明。
作为电影创作核心的“内心世界表达”,其对接的“电影之梦”,便是在不完美的二重性并立与随之生成的痛苦中,得以塑造出来。
电影创作的内容,绝对不是完美的“甜梦”,而是带有黑暗色调的个人私密化之梦,是复杂内心的体现,且不具备太大的客观正确性。
事实上,在表现艺术家的作品中,强调创作动力的绝对私密,突出驱动源头与呈现对象的个体情感,并将之定性为“非绝对普世性正确”,说明创作情绪的“浓烈而不必须积极”,是不罕见的思路。
《爆裂鼓手》的光头指挥,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施压与逼迫中,让男主角从绝望中激发垂死挣扎与愤怒难当的激烈情绪,化作打鼓的内在力度。
而《莫扎特传》里,导演先是给出了一个在普世观念里可算是顽劣、自私、淫荡的莫扎特,而驱动他完成后半段---即三大歌剧的后两部组成的巅峰期---创作灵感结果的,却往往是父亲丧生(《魔笛》)、被丈母娘说教(《魔笛》)被“幽灵”找上门(《安魂曲》)这样的负面情绪爆发时刻。
任何打击都会让他的肉身走向毁灭,一次次积累下直到死亡,但也同样会让他的音乐创作走上顶点。
人类莫扎特可以被随时以生命的形式打败,但音乐神童莫扎特却会将一切当作艺术升腾的养料,这正是莫扎特区别于“不正确的人身”而具有的音乐圣子amadus的神性,也是萨里耶利以人类立场在属于神子莫扎特的音乐领域对抗他的必然失败原因。
到最后,萨里耶利不得不臣服于《安魂曲》的伟大,代笔记录乐谱,并在老年后精神失常,战胜了人类莫扎特,将他抛到了坟地里,但却会被神子莫扎特惩罚---让他失常,在空中嘲笑他此刻自以为战胜神明的愚蠢,就像曾经嘲笑他的音乐,而在音乐上,则以自己的万古流芳折辱他被淹没于历史的平庸之作,妄图盗取的《安魂曲》终究物归原主。
可见,对艺术的理解,电影人其实存在着一定的共识。
可以说,电影是梦,但梦却未必都是好梦。
将梦与梦中所感,用画面的方式呈现出来,完成对纯粹自我的聚焦下的反映,便是“电影”的本质目的。
而对于斯皮尔伯格来说,电影,无疑便是他的“树洞”。
3 ) 《法貝爾曼》:影像構築源自生活,成長體悟源自家庭
近幾年大導演建構自身童年回憶作品熱潮中,主題啟蒙最關乎電影,火侯掌握也最為勻稱的一部。
從小便拿起8厘米家庭錄像機拍攝,高中換拿起16厘米拍紀錄片電影,家庭之於藝術,藝術之於家庭,影像的創作、光影的構築皆源自於生活,父母給予極大的自由讓他把持著他的「嗜好」,然而當嗜好不再只是嗜好,而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時,便是藝術家必須在家庭與藝術之間拉扯的時候。
影像的捕捉讓他在構築美好的過程,發掘了不美好的事實,影像不會說謊,但是剪接可以說謊,在充滿愛的環境下終究得面對原生家庭不完美的現實。
母親的秘密是他初嘗構築影像時必須面對的酸甜苦辣,再者猶太人的身份讓他在加州的高中顯的格格不入,直到再次拿起了攝影機勇抱影像,生活才又開始有了顏色。
然而每一次逐夢的心血要呈現在眾人面前時,現實的重擊總是在該開心的時刻變的百感交集。
老史大可通篇以迷影情懷視角去講一路成為大導演的過程,但他最後仍然以兒時最私人的複雜家庭樣貌,去讓觀眾感同身受母親內心所苦、父親內心所苦、自身受家庭、猶太人身份影響,其內心的百感交集。
這並不是什麼單純大導演自肥迷影情懷作,這是在回溯過往成長史中,創作者逐步與過往自我、父母和解的家庭故事。
這同時也是老史在調度上最無炫技氣息的電影,通篇都是原生家庭的自我解構,人物情感才是主要核心。
這部作品也要看個人是否對史匹柏特別有愛,如果有愛絕對會喜歡這部電影,如果還好就看個人感受了。
蜜雪兒威廉斯和青少年老史有幾場互動是真的想哭,在講述母親內心抑鬱之苦上,老史做到了能讓觀眾感同身受的刻畫,母親是愛他的,但她也愛沙漠、愛鳳凰城、愛班尼,放她自由才是終結抑鬱唯一的方式,蜜雪兒威廉斯的表演確實值得影后的提名,青少年老史的第一部電影演出,在大導演的調教下自然又輕盈,外型也真的神似年輕時的老史。
從鳳凰城到亞歷桑納州,最後再輾轉到加州,成長環境都在沙漠中,也不難懂為何老史第一部長片《決鬥》通篇背景都是沙漠;畢業舞會女友在車內狂噴髮膠致敬第二部長片《橫衝直撞大逃亡》;為學校拍的紀錄片《翹課日》,豔陽沙灘下男男女女的鏡頭捕捉,背景多少有《大白鯊》的既視感。
林區最後以約翰福特的身份客串,「地平線的頂部和底部視角呈現會很有趣,但是中間會很無趣」,短短的幾句忠告,便養成了大導演日後調度上的準則,永遠不要讓視角侷限。
收尾鏡頭地平線從中間調成底部格外俏皮有趣,有種準備迎向夢想,闖出自己的一片天的感覺。
《大白鯊》、《第三類接觸》、《ET》、《印第安納瓊斯》、《侏羅紀公園》、《辛德勒名單》,老史的經典實在是多的不勝枚舉,30年前的《辛德勒名單》是為自身為猶太人的身份而拍,30年後的《法貝爾曼》總算是為了家庭、為了自我,以大導演的身份下去拍。
拍出眾多經典大片的背後並沒有什麼夢幻的成長史,只有父母的愛與鼓勵,以及伴隨著愛背後不完美的原生家庭。
拍片50多年終於迎來史匹柏的私人解構,身為老史粉很開心看到了這部,拍了眾多大片依然能保持初心,在這部電影中徹徹底底的返璞歸真,不炫技、不自肥、不矯揉造作,好萊塢電影化後的半自傳作品,雖然虛虛實實還有待商確,但已明顯能感受到創作者的成長溫度與初衷。
Life can't be like a Hollywood movie, but life can dream like a Hollywood movie.★★★★☆#法貝爾曼#TheFabelmans #蜜雪兒威廉斯#保羅迪諾 #賽斯羅根#加布拉貝爾 #大衛林區#史蒂芬史匹柏 #約翰威廉斯
4 ) 《造梦之家》:八毫米摄影机承载的梦想
《造梦之家》,原名 The Fabelmans,直译为法贝尔一家,与译名不同电影里呈现的这个家并不造梦,而是使一个孩子的梦想毁灭。
这是一部关于梦想与家庭如何抉择的电影,也是一场属于导演斯皮尔伯格的迷影梦。
《造梦之家》延续 了斯皮尔伯格以往形式主义风格的影片,制造了一个类似真实的模拟世界——导演将大部分现实的残忍模糊化,高饱和度的画面色彩、大面积柔光营造的梦幻氛围,种种细节提醒着作为观众的我们,这只是一个人造的理想世界。
斯皮尔伯格可谓是好莱坞当代最能兼具商业性与艺术性的导演,近两年他的电影在兼顾主流的同时增加了更多自己的表达欲。
从献给父亲的《新西区故事》到致敬自己的《造梦之家》,都是如此,后者更是将这点体现得淋漓尽致。
与以往商业片“夹带私货”式的各种隐晦表达不同,《造梦之家》用“直给”的方式将导演所想表达的用影像传达给我们,这是一部恪守着好莱坞叙事结构的《四百击》式的电影。
摄影机:每个人心里的迷影梦 摄影机是电影里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个道具,作为线索贯穿全片。
摄影机代表着热爱,代表着自由,代表着梦想。
选择梦想意味着离开,离开自己的家庭、离开熟悉的环境;选择梦想意味着失去,失去爱自己的家人、朋友,踏上一段全新未知的追梦旅程。
作为斯皮尔伯格自编自导的半自传电影,迷影经历是全片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也是其作者性的重要体现。
山米第一次拿起摄影机,仿拍了他看的第一部电影— —塞西尔·B·戴米尔导演的《戏王之王》里火车出轨撞上一辆汽车的场景,而在 1895 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的 12 部标志着电影诞生的短片里,其中就有一部短片是《火车进站》。
“火车”将两个时空连接历史与现实从而形成互文,这是山米迷影的开始,象征着他拿起摄影机开始了由“做梦”到“造梦”的转变。
斯皮尔伯格说过,他的电影几乎无不植根于家庭。
童年时家庭破裂带给斯皮尔伯格不可磨灭的影响,延续至他的一系列作品里——对幸福家庭的渴望,而《造梦之家》则是最为直观的体现。
家庭与梦想山米选择了后者,而现实里斯皮尔伯格也选择了电影。
导演的迷影经历会给观众带来共鸣,不管是真实发生,还是经过艺术加工,已经完全不重要了,我们看到的都是斯皮尔伯格作为一名造梦者想用影像传达给观众的,我们所做的仅仅是需要接收、相信、行动。
剪辑器:破碎梦想的重新拼接 库里肖夫认为电影的理念是零碎片段的组合,这些片段不完全和真实生活有关。
[1]摄影机拍摄下来的影像,只有纪录功能,通过剪辑将零碎片段重新进行排列组合,才是创造性的电影艺术。
剪辑器在影片中出现了两次,都是在山米家庭关系发生变化的转折点。
第一次出现是山米在剪辑家庭露营电影时,发现了母亲与伯尼叔叔“亲密”关系,他选择了隐瞒,为母亲保守秘密。
而被丢弃的删减片段,却在山米与母亲之间留下了难以避免的隔阂,于是他卖掉了摄影机,他的梦想破碎了。
第二次出现是在父母提出离婚后,山米兄妹两人在剪辑器前看剪好的“逃课日”影片。
电影是生活 的二次创作,将影像与生活分开,这是作为一个造梦者要掌握的最基础的必修课程。
正如巴赞所说:电影最终改变了生活,当然生活毕竟还是生活。
[2] 电影画面往往都是带有很强的主观目的,我们看见的仅仅是导演想传达的内容,观众在与电影的关系里是处于被动位置的。
电影里导演借山米拍摄“逃课日” 影片,经过剪辑后用稍显稚嫩的蒙太奇将霸凌自己的查德塑造成一个高大的英雄 人物,看似赞扬实则嘲讽,而作为主角的查德深知这是自己遥不可及的完美形象,从而产生了极大的心理落差,产生了自我怀疑,这是山米以导演身份用独有方式对霸凌者的一种另类反抗。
与《跳出我天地》、《弱点》等同样围绕家庭与梦想的励志电影不同,没有被家人理解、成功追梦皆大欢喜的结局,《造梦之家》并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励志电影,而是斯皮尔伯格的一部伪纪录片式的私人影像。
正如《四百击》里的安托万是遇见巴赞前的问题青年特吕弗的缩影,《造梦之家》里的山米是已过古稀之年的斯皮尔伯格回忆往昔时的救赎,就像《天堂电影院》里的托托在长大成为一名导演以后,看着放映机里一帧帧亲吻镜头拼接而成的影片,想起挚友及引路人阿尔弗雷多时的声泪俱下。
胶片:成长的忠实记录者 纵观全片,摄影机与剪辑器是山米的玩伴,而胶片则记录着山米的成长。
开篇年幼的山米问什么是电影时,父亲解释是视觉暂留原理,母亲说电影是难以忘怀的梦,理性与感性两种不同的回答也体现了斯皮尔伯格生涯里截然不同的电影风格,显然《造梦之家》是纯粹而感性的后者。
我以为《造梦之家》是斯皮尔伯格亲手建造的一个童话故事,故事里的少年追梦旅程的开始一帆风顺,最大的烦恼只是父亲对自己的梦想当成爱好与第一次求爱的失败,电影的最后山米见完偶像约翰·福特(大卫·林奇饰)之后戛然而止,开放式的结局引发我们无限遐想——那么现实呢?
《造梦之家》是斯皮尔伯格作为过来人给像自己一样热爱电影的人造的梦,这个梦永远都是进行时,而梦 想背后的路,只有自己走过才能书写。
5 ) 比内疚更浪费的情绪,所有人都会挺过去 ,以及你遇到了最好的女孩
人生其实是个无解的事,当然除非你拥有足够的资源。
孑然一身当然好,但人如无意外都有被爱和爱人的渴望,都有组成羁绊的需求,所以家庭一直都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组成家庭必然产生责任,但这个责任却无法一刀切开,一分为二,一人挣一半的钱,干一半的家务,吃一半的饭,生一半的孩子。
因此必然有人要出门挣钱,有人要照料家里。
当然有得是男性因为自己是挣钱主力而颐指气使的,但Burt显然不在此列,直到最后你都会觉得作为丈夫的角色,这个人是完美的。
能够满足家里的开销,并且不断提升生活质量,从不自大,体贴妻子,情绪稳定,尊重孩子。
相比之下问题似乎出在Mitzi身上。
但有一点是无法忽视的,那就是虽然同属为家庭出力,但Burt在挣钱的同时,是能够实现自身价值的,而Mitzi在照顾家里的时候,却需要将自己热爱的音乐事业逐步放弃,变成了爱好。
这也是为什么当父亲将Sammy的电影热忱称作爱好时候,Mitzi能够感同身受,并站在Sammy一边。
Burt曾经建议过Mitzi继续事业,但Mitzi选择了牺牲,为了他们的家庭。
其实他们婚姻的问题并不是Bennie,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婚姻之所以能延续这么久,还多亏了Bennie。
他是Mitzi心中唯一的一点微光,是她能够继续下去的勇气。
所以当第二次搬到加州,失去Bennie的Mitzi终于崩溃了。
持续的牺牲让她觉得不值,而离开的想法又让她内疚。
她一边觉得所有人对不起她,一边觉得她对不起所有人。
在这两种情绪的挤压中,她找不到出口。
她找不到,因为没有出口,这本就是个无解的命题。
婚姻对女性的困境就是牺牲似乎是必然的。
女性一旦走入婚姻,一旦决定孕育生命,就势必面临着身体的虚弱和长达数月甚至一年的恢复期,这在职场上是无法规避的劣势。
因此男性作为家庭经济的来源,而女性维护家庭稳定,从组织分工上的确是最合理的。
但问题就是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并不意味着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女性的个人价值往往就会被忽视,甚至被否定。
因此身为女性必然面临在家庭和个人之间只能选其一的局面,而这一点在男性身上并不存在。
男性完全可以兼容并包,只是大多数人两个都选了,但两个都弄不好罢了。
在与孩子摊牌的时候,虽然两人都极力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但依然难以平复他们的情绪,所有人都觉得天塌了。
当然Sammy除外,因为他早就知道了。
但其实所有人都会挺过去的。
就像Sammy被Monica甩掉之后,Mitzi跟他说的一样。
悲伤并不是坏的情绪,怨恨才是。
Sammy有一个很好的爸爸,也有一个很好的妈妈,虽然他们不再在一起了。
但他最幸运的是,他有一段很好的初恋。
Monica积极,阳光,主动,并且知道自己要什么。
她如此斩钉截铁的拒绝了Sammy,避免了他重蹈父亲的覆辙。
不要要求女孩放弃自己的学业,和你离开。
你或许承担得起她的生活,但你承担不起她的牺牲。
因为那是种比内疚更浪费的情绪。
6 ) 献给电影的电影
sammy用超8拍出第一部影片时,他把他的电影捧在了手心里。
光影魔法的梦在这个家庭中诞生,想要摄影机就有摄影机,想要剪辑台就有剪辑台,刚进入行业就见到了梦想中的大导演,这个大导演还是大卫林奇,谁能不羡慕…影片的每一帧都很真诚、渗透了浓烈的个人情感,画面、声音、节奏把欢乐、悲伤的回忆,成长的历程,梦想的破灭与坚持,家庭与艺术中夹击背叛分崩离析,一切都那么饱满,令我感动。
和《当我望向你的时候》一样,强大的心脏将自己剥开展现给观众,在“造梦之家”放下了自己的生活和对当下电影产业的思考,收起了锋芒把地平线放到了中间,柔软的直觉依然可以让我看到小时候看《E·T》时对这个传奇导演的想象。
不仅仅是对电影的情书了,他作为“电影小子”,已经把电影写进了他的生命里。
做梦是爱好,也可以是我们为之奋斗一生的梦想,兼具史诗感的家庭故事献给所有热爱电影的人们!
7 ) 这封情书有点甜
《造梦之家》是近年来最好的“电影情书”,也是斯皮尔伯格作为电影大师相对真诚的自我剖析和总结。
影片在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这是很多同类型电影处理不当的地方。
简单的例子就是《好莱坞往事》和《巴比伦》。
《好莱坞往事》偏重昆汀个人视角下的好莱坞电影业和“曼森事件”,通过真实和虚构的融合,在历史真实事件的基础上重构出另一个真实。
这个经过重构的现实洋溢着导演对电影这个小圈子的疯狂热爱,在客观上疏离了观众的个人体验。
这是导演个人的电影幻想,与观众无关。
《巴比伦》的叙事野心非常庞大,旨在描绘好莱坞电影工业发展史。
导演达米恩·查泽雷塑造了一个热爱电影的底层墨西哥移民,投身电影业,历经默片、有声电影、彩色电影三个时代,见证了好莱坞发展的辉煌,也展现了好莱坞阴暗的角落,通过对好莱坞亮面与暗面不加修饰的展露,抒发电影人在时代潮流之中的脆弱。
是的,电影有其丰厚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资产,但对多数观众而言,电影只是娱乐。
《巴比伦》所要表达的永恒感在“当下”的电影潮流前显得不合时宜。
这个梦过于宏大飘渺,个人零碎的情绪显得毫无意义。
《造梦之家》是一部传记电影,有着无可争辩的客观性:导演斯皮尔伯格个人的电影成长史。
如果说,电影大师这个称号的内在意义是什么,那就是它代表了“活着的电影史”。
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斯皮尔伯格的伟大毋庸置疑。
他题材多变,电影类型涵盖科幻、冒险、惊悚、历史、战争、传记等。
同时,他是传统特效和CGI特效结合的推动者,《侏罗纪公园》开创了好莱坞大制作电影的先河。
在《造梦之家》中,斯皮尔伯格着重刻画了其日后电影成就的征兆。
电影主人公Fabelman从小对影像有着敏锐的感知力,当他一遍又一遍翻看自己的首部战争片时,他发现,自己所拍摄的战斗场面过于虚假,没有任何感染力。
经过一番研究,他发现特效的秘密:为了增加影像的真实感,电影需要特效,特效虽然是人为的虚假,却能还原影像的真实。
真实的生活是无序和单调的,由于我们生活其中,所以感受不到;一旦生活的片段被记录下来放在银幕上,这种真实化的无聊感便被放大。
电影需要重点,或者说,任何艺术需要对观众注意力的引导,而这就是特效的意义。
断臂维纳斯的断臂、蒙娜丽莎的微笑,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特效?
同时,Fabelman的犹太人身份在片中饱受凌辱,这也为日后斯皮尔伯格电影中的犹太主义-视角埋下伏笔。
《造梦之家》的客观性建立在斯皮尔伯格的个人经历上,而其主观性来自于斯皮尔伯格个人对其经历的阐释。
换句话说,生活的经验是客观实存的,生活的意义是主观赋予的。
意义虚化成了梦,意义实化便是家;家是梦的摇篮。
《造梦之家》中,主人公Fabelman(也就是斯皮尔伯格)成长的载体是他的家庭,这是他生活的兆始。
电影的英文名字《The Fabelmans》直译就是法贝尔曼一家。
斯皮尔伯格不厌其烦地向观众构建家的含义,在剧作技巧上是比较保守的。
毕竟family这个主题经由唐老大的发掘,已经被玩烂了,当下影迷是比较害怕family的。
但是,近年来奥斯卡的评奖标准恰恰侧重于“家庭”这个概念。
远的不说,今年奥斯卡最佳电影《鲸》就是一部主打家庭温情和自我救赎的电影。
所以,将梦与家绑定,也是最为保险、通用的做法。
一方面,家很容易理解,另一方面,家很容易得奖。
从一层意义上讲,斯皮尔伯格实在是太懂奥斯卡了。
那么,最后只有一个问题:大师的家和普通的家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答案是:没有。
斯皮尔伯格为《造梦之家》构建的家依然是老掉牙式的:中产家庭感情为纽带,父母出轨为矛盾,孩子青春为契机,完成所有人的自我救赎和妥协。
最终,Fabelman从最初对梦的恐惧完成了对梦的捕捉,Fabelman在家庭的支撑下,开始自己的逐梦之路。
令人惊喜的是,影片最后,对主角之梦完成敲打的,正是由导演大卫·林奇客串的伟大导演。
大卫·林奇对超现实梦境的影像构建独具一格。
当老头子抽着雪茄,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教育斯皮尔伯格时,这个场景实在梦幻。
总的来说,《造梦之家》平实、易懂,富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没有陷入导演个人的偏执视角,也没有极端追求假大空的历史叙事,在如今这个极端追求资本回报率的电影市场里,当属清流。
或者,某种意义上而言,正是因为斯皮尔伯格经受了市场和艺术的双重考验,才有资格摆出《造梦之家》这样的电影。
8 ) 塑造人生的梦
“当地平线在底部,会很有趣;当地平线在顶部,会很有趣;当地平线在中间时,就无聊死了!
”
我想,斯皮尔伯格导演真的做到了“是什么时候就该做什么时候的事”。
想想前几年冯小刚的《只有芸知道》,也像做了一场梦。
同样是技术流派,斯皮尔伯格目前也开始返璞归真了。
这部《造梦之家》是斯皮尔伯格写给电影的情书,也是写给自己的情书。
就我的理解,这场梦,本就是他自己的人生。
作为斯皮尔伯格导演的自传电影,《造梦之家》就是满满的私货。
但是这一口口的私货却格外甘甜可口。
也许每一帧都平平无奇,也许每一帧都意义非凡。
没有过多的复杂蒙太奇,就是平铺直叙。
没有什么花言巧语,就是平平常常的电影人生。
每一位主演的表演都让我看到了斯皮尔伯格导演家庭的真实写照。
无论是保罗达诺“突破以往精神病刻板印象”的慈祥爸爸,还是米歇尔威廉姆斯时而癫狂时而娇嫩的妈妈,这就是斯皮尔伯格想拍的,斯导的家庭就是这样的,至少,他想让观众看到这样的一个家。
所以说,《造梦之家》是造梦,不是做梦。
斯皮尔伯格的人生当然是自己活的,他眼中的自己,就是影片中的自己。
人生真是五味杂陈,人生真是一点一滴的细节,不会像电影中只剪辑需要的和重要的节点,甚至你想控制电影呈现哪种情绪,剩下的是可以删除的。
他为电影而活,也最终活成了电影。
然而最后,梦不一定是美梦,家也终于打破了脆弱的温馨,他再次拿起摄影机,屈服于命运残忍的召唤,电影与生活无限重叠……最后一个镜头,地平线本来好好在屏幕中间固定着,却又在最后一秒调皮地掉到了底部,露出一片广阔的天地。
像是斯导在和观众对话,和电影对话,和自己对话。
我的情书,你的名字。
情书上,尽是电影。
9 ) 电影的特权
说到明年奥斯卡颁奖季的最大热门,当属好莱坞名导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返璞归真,继续与老搭档托尼·库什纳(《慕尼黑》《林肯》《西区故事》)合作编剧的半自传式电影《造梦之家》。
故事基于斯皮尔伯格的人生经历,主要聚焦于男主角萨米从孩童到青年时期,与父母和姐妹们欢笑与忧伤交织的家庭关系,对电影的无限热爱和追寻梦想,以及反犹主义盛行的校园生活、青春的萌动和困顿。
《造梦之家》已获第80届金球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编剧和最佳原创配乐等5项提名,早前更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获得分量最重的奖项,由观众票选产生的「人民选择奖」,绝对是第95届奥斯卡最佳电影宝座的有力争夺者。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拍摄了《火车进站》,标志着电影的诞生。
在那将近一分钟的时间里,火车的轰鸣、从远景驶近、在车站等待和上落的旅客,如今看来似乎毫无修饰剪辑的朴素影像却彻底震撼了当时巴黎的观众。
火车因此成为了电影史上最早出现、经久不息的「奇观」。
《火车进站》虽然没有动用任何剧本、拍摄技巧,但它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客观真实,因为在被火车仿佛要迎面相撞的逼真感所吓坏的同时,我们同样惊讶于月台上乘客们的淡定克制,他们难道不知道不远处一台巨大的机器正在拍摄并捕捉他们的一举一动吗?
实际上这些往来走动的「乘客」当然意识到摄影机的存在,而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卢米埃尔兄弟找来的亲朋好友,假装是互不相识的乘客,以营造真实陌生的月台效果。
应该说,这些乘客是电影史最早的演员,在拍摄技术尚未跟上的时代,「表演」便率先在电影中发挥出重演客观事实的重要作用。
之所以特意提及《火车进站》,不仅因为斯皮尔伯格在《造梦之家》开首同样以《戏王之王》里火车出轨、与车辆激烈相撞的灾难奇观作为促使小萨米与电影结缘的源头,更为关键的点在于,自电影诞生之初,除纪录客观事实/现实能令观众惊呼连连之外,「造假」也一样可以达到如此效果。
若说卢米埃尔兄弟在拍摄时仍需要预留在现场等待火车进入月台的时间,那么《戏王之王》利用发展长达半世纪的摄影、剪辑合成等电影语言和技法,能在安全无虞的情况下拍出载满旅客的火车倾轧相撞的惨烈一幕,而作为道具和演员的车与人皆完好无损。
年幼的萨米对电影的最初,亦是影响其一生(创作风格)的印象定格于人造的「灾难」。
回到家后,他拿着母亲米齐(米歇尔·威廉姆斯)送给他的第一台8毫米摄影机,用上父亲伯特(保罗·达诺)制作的微缩火车模型,反复模拟电影中火车脱轨相撞的场景。
在这里,斯皮尔伯格运用大量主观视角表现男孩对火车迎面驶来的惊奇神情、男孩用自己双手充当放映机的银幕并对着影像出神,这时他已从普通观众角度领略到电影「造假-造梦」的特质与魅力,但却是首次从导演位置体验电影赋予的「掌控一切」的特权。
斯皮尔伯格从影片一开始便毫不諱言地向我们展示电影不可能不存在「伪造」的成分,尤其对于一位富有想象力的男孩来说,如此之「假」恰好与充满童真的幻想世界相互联系,而电影也成为了萨米将日常经验转化为脑内的奇思妙想,再铭刻于影像的「事件」载体:去医院拔牙(多数小孩子的童年恶梦)、木乃伊、骷髅鬼怪,他的姐妹、父母亲成为了最初的演员和「受其惊吓」的观众。
正如当年卢米埃尔兄弟动员亲朋拍成的《火车进站》是为世界电影(史)之开端(但从本质上说仍是一部家庭电影),萨米利用轻便器材,集结家庭成员之力一同制作电影的过程可被视为其个人(以家族为基础的小作坊)电影史的诞生,而这也是片名「造梦之家」(The Fabelmans)所蕴含的深层含义:「家庭」往往是关于电影、关于创作的梦想起源。
踏入青春期,萨米(加布·拉贝尔)的创作环境逐渐脱离局促狭窄的家里,可供临场调度指挥的空间变得宽广,一众群演也由一开始的父母姐妹变为学校的同学。
与此同时,身为导演、编剧、剪辑的萨米在电影制作的造诣亦在不断丰富和延伸,所参与的拍摄工作变得更多更繁杂,包括指导演员表演和走位、镜头调度、打光配乐、枯燥的剪辑工作,甚至还得想办法解决场景不够逼真的问题。
例如,萨米从《双虎屠龙》中获得启发,参加童军夏令营拍摄的第一部西部片,他在胶片上穿孔,制造出牛仔开枪射击的「特效」,配合抑扬顿挫的背景音乐,礼堂内的观众纷纷被那扣人心弦的情节和荡气回肠的正邪对决所深深慑服。
在配乐、特效和镜头剪辑的帮助下,那些看上去拍得很稚嫩、很假的原始影像素材组合起来后竟令观众们沉浸其中,而这恰恰是一个「由假入梦」的观影体验,当导演施放的光影魔法与人们的情感、想象或欲望实现交融,那么观众便会不自觉地为眼前的所见所闻(尽管是虚假的情节和布景)而揪心着迷,好像置身于自己就是银幕里的主角,周遭发生的一切有别于日常生活,却又无比熟悉的梦境。
由孩童到青年,萨米实际经历着由呆望着银幕「发梦」到自己动手拍电影为大众「造梦」的蜕变,斯皮尔伯格将萨米摄制技艺的日益精进,与电影梦和家庭现实之间的割裂,乃至成长过程遭遇到的歧视(反犹主义)、好奇和迷惘(性萌动)并置,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为了安抚母亲失去至亲的悲痛,萨米用摄影机纪录下一家人前往野外露营的欢声笑语,在剪辑素材时,意外发现自己的摄影机拍到了某种「不可见」的、不为世俗允许的情感连系。
而这正是身为导演和剪辑的萨米所享特权的鲜明体现,唯有他知道在一个个看似轻松休闲的笑脸、欢乐时刻背后隐藏着足以引致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瞬间崩塌的「真相」。
于是,在最终呈现的家庭录像里,萨米仅仅留下了母亲的灿烂笑容,以及月光之下的婀娜舞姿,如此美好、令人动容的回忆与形象,然而我们都知道,这样「如梦似幻」的母亲是经过导演精心剪辑创造出来的,而母亲与父亲挚友伯尼(塞斯·罗根)暗生情愫、可能造成家庭破裂的「有害」片段无一例外被剔除了。
这或许是萨米第一次对电影赋予的特权感到厌恶,因为无论萨米对影像素材的裁剪合成技术如何精湛,但他没办法阻止父亲因工作之故频频搬家、冷落家庭,压抑已久的母亲移情别恋的事实,特别是当他一遍又一遍倒带回看母亲面对情人时露出的笑容是如此的真挚。
尽管如此,萨米只能保守秘密,这一刻曾经无比钟爱的电影已成为暗自表达愁绪的媒介。
在战争片里,萨米不由自主地将自己对母亲出轨的困惑不解融入面对死去战友的幸存军官心境,这位军官因为下达了错误的命令而致使弟兄们落入纳粹陷阱,全军覆没。
军官既可以指代(在家人眼中)做错决定的母亲,亦可以指代意识到影像的危险——摄影机前没有秘密可言——而选择自我惩罚的萨米。
讽刺的是,观众为银幕上的惊险和暴力发出赞叹和欢呼,却无从知晓这是以一个少年对逐渐分崩离析的家庭生活的绝望情绪为养分。
观众的惊叹又何尝不是一种对创作者本身的暴力?
纵然才华横溢的萨米控制得了电影「拍什么」「怎么拍」(斯皮尔伯格特意安排了一场戏,在萨米的镜头下,一家人搬进新家的温馨画面,下一幕却是现实父母陷入离婚边缘),但终究控制不了生活与成长过程中突如其来的残酷变故。
电影在「造梦」和「现实」层面的不可分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果说「家庭电影」(宛如童话般的纪录片)满足了父母亲、姐妹们对于幸福家庭、亲子关系的要求,那么对既是导演又是儿子的萨米来说,为观众提供欢笑和希望所付出的代价却是独知真相后难以释怀的悲伤和忧郁,而在现实中拥有缺点的母亲也成为萨米(斯皮尔伯格)未来在银幕上创作出「完美母亲」的缪斯。
萨米为自己拍到了不该被拍到的内容而深感不安,卖掉摄影机不再拍摄。
主动放弃拍片、驰骋光影之海的「特权」令萨米在新环境难以适应,正如电影一旦失去了造梦的功能,人们(包括创作者自己)不也失去了从象征永恒的银幕里获得应对瞬息万变、冷峻无情的现实世界的力量吗?
故此,当萨米鼓起勇气再次拿起摄影机开始拍摄「逃学日」,同时亦因艺术与生活的潜在张力而生生撕扯出一个供萨米独自面对、承受(破碎家庭、校园暴力、失恋)伤痛的私人空间:追求艺术恰恰是「自私而孤独」的。
高中舞会上放映的校园纪录片从表面上看是一场肆意挥洒肉体和汗水的青春奇观,但萨米的这次「造梦」不再是让观众重获面对艰苦生活的良善力量,而是反过来利用影像里潜藏的危险(摄影机看穿了人们注意不到的「闪光点」),对那些以自己的欲望和憎恨霸凌他人的反犹主义同学「明褒暗贬」,透过在银幕上制造一个永远无法触及的英雄形象折磨羞辱对方。
斯皮尔伯格借此机会告诉我们,电影并不是只有美好纯真的一面,它同样可以是自我中心的、具有攻击性的利器。
乔登皮尔在《不》里向我们发出警告,奇观是如何把任何试图捕捉、挑战它权威的观众和电影人活生生吞噬;对斯皮尔伯格而言,也正是令人目不转睛的「奇观」引领他踏上追寻电影梦的旅程,所以老斯认为奇观本身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控制和驾驭脑袋中那些关于电影和艺术的疯狂想法。
正如萨米和年迈的舅舅鲍里斯(贾德·赫希)交谈,鲍里斯过去曾在马戏团与凶猛的动物一同表演,萨米问:「把脑子塞进狮子嘴里是艺术吗?
」 舅舅听后大笑,回应道:「不,把脑袋伸到狮子嘴里只是胆子大,保证狮子不会咬掉你的脑袋才是艺术。
」可以说,《造梦之家》不仅作为斯皮尔伯格的半自传电影,更是一场「电影与人」的奇观:摄影机绝无偏袒地记录下生活的一切,不论是美好的还是丑恶的,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老斯拒绝被贴上「这是我的私人记忆和情感,不准擅闯禁地」的怀旧标签,那个在银幕前为光影的魔力所震撼的孩子,那个拿着摄影机到处捕捉微小事物的少年,可以是银幕外的每一位观众。
人物们平等地享有秘密,而电影、影像成为了彼此交换秘密的暗室,所有的悲伤、欢乐、焦虑、痛苦、遗憾都在其中得以体现,并且被镜头转化为源源不断的生命能量。
推动萨米去重新相信梦想、追寻梦想的或许不再是小时候的单纯和激情,而是对越来越糟糕的现实生活的麻木和绝望,这也排除了电影一味缅怀过去的倾向,更多是属于当下的语言、理想和行动。
对大多数人来说,在生活的洪流面前,电影一点也不重要;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如果连电影也失去了,那就什么也没有了。
影片最后,大卫林奇饰演的约翰福特对萨米说:「当地平线在底部,会很有趣;当地平线在顶部,会很有趣;当地平线在中间时,就无聊死了!
」即使生活、成长再怎么残酷,都请不要放弃「抬头」或「低头」探索未知的好奇心,去记录、去表达、去造梦/追梦,这既是约翰福特、大卫林奇、斯皮尔伯格给予我们的真诚忠告,又是电影赋予所有人的「特权」。
本文首发于「虹膜」
10 ) 《造梦之家》短评之字数超了……
8.5/10,是一部贯彻着“交织”的电影。
首先分别由父母从理/感性的角度解释“电影”的本质,之后整个电影就是个人经历和影史发展的交织,从类“火车进站”,到30s开始的传统西部片、战后电影,最后到60s兴起的导演大卫·林奇本人,交织于自己/萨米的童年、少年和最后青年时期见到自己的偶像John Ford,甚至包括老斯本人过去多部影像的影子也交织在其中老斯调度没啥好说的,已入化境,不会被质疑也不可能被质疑全片最喜欢的两个片段:萨米发现了母亲的背叛,在不解和愤怒过去后,在影像的作用下,他最后原谅了母亲,因为在影像里,他终于看见母亲真正快乐的样子,也是通过影像,萨米和母亲才敞开心扉、谅解彼此;当其他孩子知道这件事后,萨米却毫无反应,镜子里的他的眼睛,就像镜子本身,也像一台摄像机,客观地注视也记录着这一切,而在这一刻,导演本人和萨米真正模糊在一起了有意思的转折:萨米被告知艺术和家人不能兼得,他却用影像和母亲完成和解;萨米被告知电影不是生活,导演本人却拍下了这部半自传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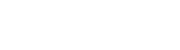














































The art will rip you apart. 胶卷是记录的介质。几处私密的闲笔,生活与影像是有鸿沟而带来的独属于那个年代的情绪认知,地平线的革命,老斯在镜头后面忠实地还原着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间的流速一如过往。电影里很少有去电影院的剧情,因为影响人的银幕体验可能只需要那一次,也就是明白超级八里面那场火车相撞的戏份对他来说有多重要,就像妈妈一定要去追那场龙卷风。大工至拙的作品。大卫林奇本色出演。
大导私人回忆录。透过影像之门拼凑生活本真面目,揭开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家庭秘闻,于电光火石间回溯昔日童年光影旧梦。电影是造梦的艺术,而他则是为千千万万观众造梦的人。令人艳羡的家庭条件和顺遂的从影之路。
这根本不是斯皮尔伯格的个人传记,这是斯皮尔伯格对电影的反思。电影会带来噩梦,会带来破碎,会带来与预期相反的后果。伴随艺术的不只是功成名就,还是撕碎——撕碎家庭,撕碎爱的人,撕碎本该和谐的一切。但斯皮尔伯格在暮年之时还是将毕业时的那段插曲拍成了电影,还是“让地平线位于画面的底部”。这便是他对电影反思的结果——因为热爱,无怨无悔。
技术上还是一如既往的无懈可击,但我花了2个半小时看完全片也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关心斯皮尔伯格的童年生活。。。别人看心理医生要花钱,结果我们还要掏钱去看史皮包治疗童年家庭问题
8.7/10 #AMC 最佳之处莫过于丝毫没有“浪漫化”电影的痕迹,电影始终是伴随着生活的高低起伏,辅助于记忆以形成某种“形态”(正如吵架段落时男主看到自己手持摄影机的幻觉),并通过生活中不同情景以切换不同的调度与风格来契合各类电影类型(剧情/歌舞/爱情/西部,或默片),此外不乏通过私人细节与回忆来印证数十年来电影学界的各类母题(电影作为技术/仪器/观看方式,摄像机作为“揭露”真相的眼睛,影院的黑暗作为包庇Obscenity的条件,以及最后点滴的对“工业”的提及),电影作为一种“实体”当然不是不可或缺的,但“电影”作为一种抽象的存在却无处不在,斯皮尔伯格并未沉溺于怀旧或溺爱(最后和林奇扮演的约翰福特的桥段甚至显出了他的叛逆:我就把水平线放在中间拍),而是伴随着浓烈的哀愁与不做作的复杂。可惜之处在于节奏和结构都有些琐碎和混乱。
老牌导演斯皮尔伯格的半自传电影,50年代末孩子就能用超8、16mm彩色片拍家庭电影的,也就是美国战后的那代人了。片子中规中矩,只是结尾主角去见大卫林奇饰演的大导演约翰福特一场,十分精彩!他说:「当地平线在底部,会很有趣;当地平线在顶部,会很有趣;当地平线在中间时,就无聊死了!」美国人从来认为“导演就是最知道镜头摆在哪里的人”,这就是忠告!
之前看过,没看完
好吧,懂了,大导演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成长在普通的家庭。好无聊啊
前一半真的不太吸引我……全靠中间drama的Monika 把我乐开花,还有结尾见到大神的片段+镜头上摇多加一星。
有一些短暂的生动,但是整体如预期般平淡。
最后福特那段最精彩,“最重要的是水平线”,然后导演突然就悟了。最后一个镜头手一抖,把地平线从中间移到画面下部。
戏内是小少爷美国梦,戏外是大导演凡尔赛。
看你爸妈送你摄像机看你拍电影看你被打看你妈出轨看你剪电影,看你把地平线放在底部,看你把地平线放在顶部,看你片尾字幕,看崩溃了,,,真自恋啊斯皮尔伯格,,,中产犹太白男
1、不知是否夹带私货、不愿舍弃,总之最终效果是冗长的,近于流水账;2、斯导的人生当然也有痛苦,但比之很多人,都太顺了,顺到那些挫折都快不成立了;3、米歇尔·威廉姆斯的表演,着实神经兮兮,神经质已成冲奖的捷径了吗?
近年的导演真喜欢拍半自传故事。老斯竟然不制造梦幻了,电影的力量没有被夸大,却觉得更深入内心了。大卫林奇演福特笑死。
三星半,确实是很私人的一部电影,就像在看老斯的家庭录像,但演员的感染力还是挺强的,如果观众共情力比较强,应该还是会挺喜欢的。
从母亲那遗传艺术天分,从父亲那遗传理智情感。母亲去追求幸福真的是太好了,从小开始拍摄真的是太好了~不要为了政治正确在主角里加黑人也是太好了。用八毫米回看母亲的秘密,米歇尔的表演真的是充满细节。
当一个导演开始自哀自怨拍自己人生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视作江郎才尽呢。篇幅长,梦想、家庭、青春、恋人,什么都说了,但作为“电影人生”的传记片,电影和其余的线却都结合不到一块去,拍电影的线又不够出彩,只有母亲那条线是最饱满的
艺术即是不确定,镜头是捕捉艺术的语言。如此深度的内核居然变成花两个半小时讲老套的家庭成长故事。剧本节奏成大问题,全员演技掉线,在影院我都想两倍速观看。
“造梦之家”并不造梦,略有些惊奇的是,斯皮尔伯格讲述的是梦一次又一次在与现实的同行和夹击中背叛自己的故事。最钟爱的媒介记下了分崩离析的种子,每一次首映都带着额外的愁绪。电影究竟重不重要?一点也不重要,因为在生活的洪流面前它什么也不是。但又好像没有更重要的事了,因为如果连它也失去了,那我们或许确实什么也没有了。驱使我们重新相信梦想的其实并非激情,而是绝望。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