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魂》剧情介绍
阿川(张孝全 饰)是一位性格十分温和的男子,某一日,正在工作的他忽然昏倒,然而经医生检查后发现身体并无异状,医生诊断阿川有可能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阿川回到了老家疗养,在那里生活着他的父亲王伯伯(王羽 饰)和姐姐小芸(黄湘琪 饰)。让王伯伯没有想到的是,阿川竟然杀死了小芸。 王伯伯将阿川关进了小屋之中,独自处理了女儿的尸体。小芸的丈夫许久不见妻子,找上门来,就在他快要找到阿川的藏身之处时,王伯伯杀死了他。小芸和丈夫的双双失踪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两名警察锁住了王伯伯,接近了阿川所在的小屋,却反被阿川杀死。为了替儿子掩盖罪行,王伯伯顶替了全部的罪过。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李雷和韩梅梅许你万家灯火小鹿斑比:清算排山倒海思想很危险兄弟姐妹求爱大作战火女今夜林中无人入睡2活着的灵魂浪女大厨第二季迷失太空第二季神探伽利略XX内海薰最后的案件愚弄大步走灵异街11号刑事7人第七季血狼犬恋爱顾问午夜人神圣之夜:恶魔猎人我可能遇见了爱情七号房的礼物2阴宅瓦德马尔好汉三条半美人鱼之死亡湖又是一年山林绿那个外星人摩登家庭第一季时空线索家族荣誉3:家门的复活火影忍者疾风传鼬真传篇~光与暗~
《失魂》长篇影评
1 ) 没有第二个钟孟宏
《失魂》是台北电影节的赢家,金马奖上则没能入围最佳剧情片提名——但钟孟宏又入围了最佳导演。
这并不是一个偶然,或许,评委们在权衡这部电影的利弊时,显然也对它的“可读解”产生了疑问。
如果,你想问为什么,那么,你恐怕不太适合看这部电影。
因为看完这部电影,你脑海里有无数个问号和为什么。
在台湾电影一片笑脸迎客和气生财的氛围当中,《失魂》的存在是如此特别。
这部电影延续了钟孟宏的暗黑风格,深入幽谧瘆人的高山林区,那里游荡着迷失的灵魂,密布着空洞的躯壳。
《失魂》犹如一部影像化呈现精神病理学的电影,整个电影世界异样的平和,又掩藏着没有来由的杀气。
看完后,我更是感慨,《毒战》、《无人区》、《天注定》也是不断杀人各种死,但“人”并没有被真正表现,他们被安插了不同的身份,要么就是充当工具与符号。
《失魂》做到了,但更大的问题随之而来,当《失魂》尝试去挖掘这类精神病人或者精神病患者的电影人物,我们几乎无法把他们当作正常的人类来看待。
他们说话的方式,他们的精神虚空,完全是活在另一个世界(无论儿子还是老爹)。
毕竟,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它有情感理智,能压制体内的动物性——这部电影也可以看做《动物世界》或者《人与自然》,那么,植物人是不是人,精神病患者是不是人?
《失魂》一上来就告诉你,这个人不是正常人,他不为食、不求欲,更没有阴影宿怨,但是他却屡次残杀,毫不手软。
这部电影是如此缺乏动机,哪怕是尝试去切入难以形容的灵魂。
三个猎人的寓言故事,恐怕没几个人能懂。
可是,当精神病院的乐队演奏起来时,我好像又看懂了一些。
也许这并没有玄机,纯粹就是电影的魅力。
【凤凰网】
2 ) 现实与超现实的夹缝——《失魂》
艺术领域往往会发生很神奇的事情。
譬如说,从一张电影海报决定要不要看这部电影。
昨天看到鱼叔推的张孝全(近期上映《指甲刀人魔》),突然就挂念起这个虎头虎脑的原始人。
张孝全有一种天真无辜的气质,也就是说,无论他做了什么事情,只要他定睛看着你,你就会相信一切都是可被原谅的。
其实我最喜欢张孝全的侧面,从侧面可以看到额头的弧度,连接眼睑的位置深深凹陷,抬眼时候产生的额头纹和眼睑皱褶刚好呼应,过渡自然的鼻子和隐约可见棱角的脸颊,浓密鬓角处透着一股原野的气息。
我很少那么细致地看一个人和形容一个人的相貌,但对于张孝全,我在想,我该如何用尽我所有笔墨来形容这个天真有邪的男人。
我最早看张孝全的作品,应该是《孽子》里的吴敏。
顶着白先勇先生的作品改编影视,在当时的台湾可算是先锋作品,能在公视播出,也是一次非常大胆的尝试,舆论和争议非常大。
《孽子》里,张孝全的吴敏并不出色,范植伟才是天才型的演员,当时的张孝全只留给我一个模糊的形象。
到后来,名声在外的《盛夏光年》吸引了我的眼光,其实里面我最爱的是演慧嘉的杨淇。
但却发现张孝全的目光,如小兽一般闪烁着纯真的光芒,我留意到了这个演员。
后来看了《男朋友,女朋友》只记得是三个人的故事(又是三个人的故事),其他已经很模糊,但张孝全与同志电影已经脱不了干系,谁叫他原始的兽性那么诱人。
他似乎根本不应该穿西装革履,背心短裤人字拖才是他的好朋友。
(《爱的发声练习》我根本记不起来)
用了那么多笔墨来说张孝全,虽然还是意犹未尽,但我的墨水也挥洒得差不多,来说说《失魂》。
尽管我没有给出很高的分数,但不失我对电影的喜爱。
喜爱可以盖过不足。
首先,电影的画面感让人欲罢不能,虽然不像侯孝贤的《聂隐娘》那般行云流水,却又有一番扑面而来的宏伟。
当然,很大一部分得益于取景的地方。
我查阅了一下资料,没有说明取景地在哪里,但在台湾,台中这种大山里的农户应该也不在少数。
《失魂》要叙说的是怎么一个故事根本不重要,但她需要以大山的特殊来烘托人物的孤僻、逃避与包容。
父子关系是主线,围绕这条主线,表现出来的是儿子阿川人格的逃离,父亲为陌生的“儿子”掩盖罪行,儿子以新的身份来重新认识父亲。
这,就是电影的故事。
整个电影,现实与幻觉交错进行,虽然显得生涩,但也还是能表现清楚。
故事开端,阿川晕倒在寿司店的工作台,镜头反复在拍一条砧板上的鱼,继而切换各种不同形态的鱼,鱼缸中张嘴呼吸的鱼,炭烧炉上正烤着被一分为二的鱼。
阿川晕倒后,镜头定格在砧板上被削剩的鱼头和鱼骨,还依靠神经一下一下地跳动着。
鱼这个身不由己的意象,很多时候用在电影中表达着一种濒临的绝望。
醒来后,阿川说自己不是阿川,被同事送回深山老家,父亲开始了和阿川这几年来最长的一次相处。
饰演父亲的王羽先生,没有看出喜怒哀乐的表情,一脸路人的皱纹,却意外地自然。
在表达姐姐被杀的镜头,切换得我非常喜欢。
白天,姐姐手里的野草,镜头一换,变成了阿川满布鲜血的手在玩弄同一颗野草。
有影评解读鲜红花朵的特写镜头,是血色的意象,隐喻着杀戮。
这里不置可否,但是否过分解读,看来只有问导演本人。
有很多细碎的昆虫镜头,父亲和女儿在花场洒水的时候,镜头特写一朵大红花,花瓣被水浇湿塌下来压着了一只昆虫,黑夜中飞蛾的飞舞的慢镜头,都是山中特有的小生灵。
另外一个煞有介事的场景,就是阿川与送信人金士杰的对话。
一口井,不是所有的井都有底,不跳下去也永远不知道通向哪里。
通过这口井,仿佛唤醒了某种尘封的记忆,镜头切换,哭声入耳,继而呈现阿川和母亲拥抱在一起的画面。
这个场景应该是参考了舞台剧的场景切换做法。
回想起来似曾相识,陈国富的《我的美丽与哀愁》中大量用到这种超现实的手法。
走失的灵魂,大概留在了母亲自杀的路上,不肯回来。
醒来后,阿川的父亲坐床边,凝望陌生人“阿川”。
对话中得知,阿川童年亲眼目睹父亲协助母亲自杀,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阿川的第一人格主动逃离身体,用第二人格重新面对父亲。
金士杰在电影中一共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在陌生人“阿川”不停开灯关灯中现身,说自己是一个送信的,送一句来自深林另一端阿川的口信,让陌生人“阿川”暂时待在阿川的身体里,他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
我的理解是,第一人格与第二人格的间接对话,第二人格陌生人“阿川”没有要离开的意思,而第一人格阿川也没有想要回来。
第二次,就是陌生人“阿川”主动找第一人格,却没有找着,在路上看见金士杰,也就是那口无底井的场景。
父亲为掩饰陌生人“阿川”谋杀女儿事实,杀了来找寻女儿的女婿,最后丢下一句“老婆都死了三天才来”表达对女婿的不满。
在挖土消灭证据的时候,父亲梦见自己被困车内,陌生人“阿川”拿起铲子要掩埋自己。
这个梦可以看出,父亲害怕陌生人“阿川”,但他只是把陌生人“阿川”软禁起来,大概因为他相信,阿川回回来这个身体。
警察找到身上来,寻找失踪的女儿和女婿,陌生人“阿川”把饰演警察的庹宗华杀害,被梁赫群饰演的小警察小吴发现,而小吴却帮阿川父亲掩饰事实。
小吴在电影中占有不轻的戏份,那个唤醒第一人格阿川至关重要的人物。
因为他们曾经是同学,他们有过共同的美好回忆。
当然电影并不是在努力如何找回第一人格的路上,而仅仅只是在探讨第一人格为什么会消失,而第二人格为什么会出现。
第二人格通过陌生人“阿川”与父亲的日夕相处,如何重新认识父亲。
结局并不重要,但如果让我来写,可能我会让父亲杀死阿川的身体,这样,留在父亲记忆中的便是第一人格阿川,那个离开大山前,与他一起生活了20年的儿子。
但好多时候,电影表达的信息都是相对积极的。
这里,我想起了Xavier Dolan的I killed my mother,说的就是母子关系,在成长中,相互伤害中,记忆中的母亲已经不复存在。
这恰恰是一个消极的例子。
当然,在这个处理上,导演也是回归现实,只是用了超现实的手法来表现过程。
心情允许的话,可以再看一遍,但人越大,衡量价值的天秤就越会避重就轻,盲目地潜意识地往更急功近利的方向倾斜。
所以,再看一次,多数会成为一个美好的空中楼阁,永不下地。
原文出处:http://i.mtime.com/edenruan/blog/8003216/ 同为本人创作。
3 ) 失魂:超现实主义迷局
台湾电影向来不是我所关注的对象。
事实上,在获得了文化上长期的相对独立发展之后,保守和本土化的作品在吸引其他华语圈的观众上需要许多努力;反之,部分过于先锋的电影语言,于我个人来说也是有所抗拒的。
但台湾在地理位置和历史位置上所具有的优势,是许许多多成功电影人的沃土,不管是思想上还是技术上,都是很值得大陆电影去扎实学习,而不是简单借鉴的。
在我眼中,电影作为第七艺术,衡量其发展程度的唯一标准,不是看个别人有多大成就,而是看整个行业体系有没有能力持续产出具有一定水平的,高完成度的作品。
无论是作者电影还是类型片,皆是如此。
放眼台湾电影,除了对我毫无吸引力但是本身已成规模的青春/偶像片,让我念念不忘的,是苏照彬的《诡丝》和《双瞳》,还有虽然亏钱但本身质素很高的《赛德克巴莱》。
而之后,或许还会加上《失魂》这样一部电影。
导演钟孟宏我并不熟悉,但是从本片中,的确能感受到他本人的创作意图和思维方式,同时作品也并不晦涩,有着明显的类型片印记。
他在采访中阐述的对类型片的看法,我是相当赞同的:“对我而言,电影必须要让各类观众都能从中发现些‘什么’。
对缺少观影习惯的人,可以很明确地接收到这是部惊悚片,而对于电影阅听经验较丰富的观众,也能发掘出延续的部分,并产生其他解读,那便是电影的成功了。
”而我之所以有此感受,是因为最近才开始看《布达佩斯大饭店》,然后着了维斯安德森的魔。
对维斯安德森来说,他的作品或许看上去都是同样的风格同样的调调,但内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核心思想和导向。
本片也是如此。
而更有趣的是,随着影片故事的推进,观众对影片本身的欣赏角度和理解维度,也是逐渐增加的。
如果只是简单地把本片当做恐怖/惊悚片来看的话,就会失去许多乐趣。
影片开始便是张孝全饰演的阿川“失魂”,被送回老家,随后便是常见的惊悚片情节展开,比如灵魂抢占身体,比如性格大变(其实也根本没有对比,或许是故意设定如此),比如六亲不认然后手刃至亲。
但很快,从1号受害者出现之后,王羽先生的表现和反应便带给我了第一次惊喜。
明明是亲人受害,却毫不慌乱,而且主动处理尸体,从而变成了不断的滚雪球,直至崩溃……作为本片真正意义上的男主角,王羽先生虽然没有精湛的演技,却把70多年来的人生经验融入了角色之中,倍感自然。
那么本片中二元对立的究竟是想表达怎样的故事呢?
表面上,仍然有着导演所延续下来的父子亲情的探讨,而且相当的感人,甚至有少许的致郁。
而角色本身的设置,又有着城市带来的人格异化与传统之间的对抗。
但我所见的是,本片在精准把握了商业类型和作者电影之间的距离下,还似乎套了一层超现实主义的外壳。
而这层外壳,在影片中段那一口没有底的井那里,展露无遗。
在我看来,阿川是否患有精神疾病,还是真的被占据身体,都不重要,这也不是电影所讨论的内容。
本片的故事,就像是在一湖平静的池水中,投入了一颗石子一样,激起了重重涟漪。
老先生对自己的儿子不关心吗?
显然不是。
那么被杀的女儿呢?
更加不是,否则也不会对戴立忍饰演的女婿发脾气。
他是在不断地试图维护自己生活的状态不被打乱,同时也在尝试去理解阿川,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也在慢慢转变,从一个平庸走向另一个平庸。
而阿川本身,与其说是超自然,不如说是超现实。
阿川占有者的真实身份从未表露过,倒不是因为想制造秘密,而是不需要表露出来,他本身就是一个超脱而又实际的意象。
而金世杰饰演的陌生老人两次出现,也都有着重要的标记作用。
尤其是暧昧不清的台词和一口意在形之外的井,让阿川的作用从一个线索人物,转变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线索。
配合着导演所擅长的冷静叙事,让这个故事在肃杀之外,也有些许的奇幻色彩。
也就是说,片中不管是人物行为逻辑还是事情本身的逻辑关系,尽管有着些许的破绽和纰漏,但仔细想想,都是由于处在这个独特的超现实封闭环境下,从不合理向合理靠近的影子。
回到父子关系本身,直到影片最后,才将这一层关系摆上了台面,大大方方描述了这种有些畸态,实则现实的转变和联结。
父亲需要的是儿子这个意象,而不是儿子本人。
儿子也最终也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虽然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儿子。
而更有趣的是,“假如你在荒野中开着车,遇到三个看来凶神恶煞的持枪猎人要你载他们一程,放眼望去没有别人,也没有其他岔路,你会怎么做?
”这则象征着人生抉择的小故事,对于阿川和老父来说,有着些许殊途同归的意味。
老父选择不帮人,但全片中,虽然手上有多条人命,却在艰苦的执拗之后,通过自我牺牲使自己的理想国得以保全。
阿川选择帮人,可本身却是夺占身体,并且毫不留情地手刃他人,从而使整个故事驶向漩涡中心。
所以,无论怎么选择,对阿川和老父来说,其实就是两根拧在一起的芯子,也意味着一个秉性的正反两面。
也正是因此,片中不停地出现含义翻转的情节:费劲心思获取剪刀,却只是为了修弹弓,而修好的弹弓,却又成了伤人和破坏的利器;一段被折下的铁网,有着锋利的尖端,却用来挠痒痒,可是最后还是成为了戳向警察的凶器。
而一个个梦境和现实的比对,还有老父的黑历史,其所言和所行的差异,也是这盘张力十足的大棋下的诸多着眼点。
因此,如果简单地说,这是一部挖掘亲情的惊悚片,其实是少了很多乐趣的。
或许片中还有些政治隐喻,但对我来说,这种将超现实主义叠加在现实的环境下的叙事方法更加诱人。
一个故事,多个维度,这才有了所思所想所感的价值。
而这,也是许多类型片倒在从一般到顶级的路上的最大原因,也是许多作者电影倒在商业价值门口的最大原因。
或许,这也是电影观众从经验中成长的必经之路吧。
http://i.mtime.com/cydenylau/blog/7789253/
4 ) 每个镜头都是精彩
诡异的气氛。
故事刚开始,倒置的镜头。
电影想要以主角阿川——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角度叙事。
羽叔生硬的台词,面无表情,令人印象深刻。
阿川好友挣大的眼睛,微张的嘴唇,像是完成一种仪式似的念着台词,让人想起片头砧板上的鱼头。
阿川姐脸部表情特写等等气氛让人觉得诡异,甚至难受。
让我想起《狂人日记》,回乡养病,所有人都要害他,连狗都是舔着嘴角的,却看出个吃人的秘密。
也许生病的人脾气都不是很好,还带点被害妄想症。
与此相对的是片中出现的静谧的山林,让人感觉到一丝宁静。
与医生的谈话,将故事贯穿,回归现实。
阿川在山林里与送信人一起拾柴,又带来一丝轻松。
这也许是对父爱的诠释。
几个细节:变幻的风雨 不变的是山。
父亲把阿川移到了山上照顾 看完医生后阿川对父亲说要回到山上去。
最后父亲带着阿川和阿川的好友下山。
有人说羽叔是老了完全是在背台词。
换个角度来看羽叔的演绎也符合一个丧偶父子隔阂常年住在山里的父亲形象。
送信人不能不说送信人是阿川心中童年时那个父亲形象。
与童年好友一起埋藏的弹珠,阿川为制作弹弓偷拿剪刀又放回原位(还记得小时候偷拿遥控器又放回原位,影片给出一个长镜头),夜里与送信人一起拾柴,阿川确实回到了对童年的回忆当中。
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阿川用手电发出SOS信号?
)时,送信人出现了。
送信人第二次出现,阿川和他一起拾取那象征心中疑惑和不安的木柴。
可是到最后送信人却把阿川引向一口井,这口井通向现实——童年时亲眼目睹父亲帮助母亲自杀,阿川惊醒。
送信人再也没出现。
遗憾最遗憾的是故事结局,变幻的烟圈,插入的一段歌曲,父亲和阿川的对话,阿川的梦境,完全看不懂了。
要不直接文艺到底:阿川梦到了故事最后所说的那个梦境,梦醒,眼里噙着泪花。
难忘阿川站在屋顶上补漏洞 下山后羽叔脸上露出的笑 羽叔问阿川山上的兰花开得怎么样
5 ) 影片没有给答案
一向都台湾电影没有特别的关注,这部,说实话,没有特别看懂,尝试,稍微说一下吧。
阿川从台北被送回了老家乡下,因为无缘由的昏倒。
疗养期间,他杀了姐姐。
父亲问为什么,他说,他不是阿川,这身体没有灵魂,他就住进来了...父亲埋了姐姐的尸体,杀了前来寻找妻子的女婿,把阿川锁在了山顶的小屋。
很多年前,阿川的母亲就死在山顶的小屋,是父亲杀的,因为母亲身患重病,想要解脱,所以,父亲杀了母亲,小时候的阿川应该是看到了...警察来查姐姐和女婿的失踪,阿川杀了警察,父亲最后帮他顶罪,关进了监狱,后来病重,进了疗养院,阿川去探望,跟他说做了个梦:他驾着车,在山路上遇到三个拿着枪的猎人,他们想让他捎他们一程。
你会让他们上车吗?
父亲说,他不会。
阿川说,我让他们上了车,后来山路遇上了塌方,三个猎人帮忙搬开了石头,我们顺利通过了山路,猎人下车后告诉他,他很快就到出口了,后来,有一个小男孩上了车,他说,他叫阿川...影片就此结束。
是灵魂互换?
还是双重人格?
影片没有给答案。
我觉得是这样的:阿川小时候看到父亲杀了母亲,后来长大了,他一直都疏远父亲,后来大概是工作压力之类的原因,产生了另外一个人格,阿川的主人格躲了起来,所以他回到乡下,不认识姐姐,不认识父亲。
这个人格,暴戾、多疑,所以杀了姐姐。
但父亲用尽所有的一切,藏了尸、杀了人、顶了罪,为了保护这一个已经不认识自己的儿子。
他开始找阿川的主人格,在警察来抓父亲的时候,他杀了警察,他想帮这个老人...对于父亲来说,由于儿子的一直疏远,他本来就不知道这个儿子的性格,无论这个儿子里面是不是自己真正的儿子,一点都不重要,他将多年的愧疚和父爱全部爆发出来,一个中过风走路都不稳的老人,艰难地用挖土机藏尸、藏车,最后用一生的积蓄和财富去贿赂,换取顶罪,他只想要一个儿子,无论是不是真的。
最后,阿川的主人格受到感动,回来了,应该说,和另外一个人格融合了,所以说,有一个小男孩上了车,他说,他叫阿川...
6 ) 亲情“失魂”
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阿川因为小时候看到父亲杀死母亲的惨剧,所以对亲情失去了信任。
这种负面情绪长期压抑,最终导致他的“失魂”。
用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论来解释,“本我”是人最本初的欲望,在片中就是阿川对亲情的不信任以及由此产生的报复和杀戮欲;“超我”是社会的伦理道德,也就是要求阿川压制这种欲望的力量;“自我”就是在“本我”和“超我”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阿川的显性人格。
“失魂”,就是指阿川的本我突破了超我的抑制,吞噬了自我——也就是阿川的意识,充分地放纵自己的报复和杀戮欲。
由此,导致了他姐姐、姐夫和杨警官的死(姐夫虽然是父亲杀的,但却是本我阿川制造了形势迫使父亲不得不动手的,所以根本的凶手还是本我阿川)。
影片中,父亲与阿川的平静相处,对阿川的全力守护,与其倾心交谈说明了父子二人误会的根源,最终替子定罪的行为终于唤回了阿川的自我。
金马奖还是一项很有水平的奖项的,不会把自己的大奖授予一部烂片,影片最大的亮点就是实现了“技术”和“艺术”的完美结合,在挑战“头脑风暴”的同时,又传达了亲情的主体。
只不过影片的小清新风格可能不太讨喜,如果是由商业片导演来拍的话可能会更受欢迎。
7 ) 《失魂》如何“回魂”
《第四张画》让钟孟宏拿到了金马奖最佳导演奖,但好像对导演拍片环境的改善帮助并不大。
叫好不叫座的现实,让导演在为下一部电影筹措资金时依然困难重重。
导演在接受记者访问时也曾开玩笑地感叹:“为什么喜欢我电影的人,都不是有钱人?
”于是《第四张画》之后,钟孟宏拍了《失魂》,一部很特别的商业类型电影。
不过,艺术家哭穷的事也要分开来看:票房不佳投资少是真,而借着得奖的东风期待在商业上有所突破恐怕也是事实。
导演与投资方互惠也是好事,而对之前电影生涯颇顺遂且成功的钟孟宏来说进行这样的尝试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导演“仍可以在包装的底下实践自己内心想要表达的纯粹的东西”。
《失魂》是带暴力元素的惊悚心理剧。
在台湾,惊悚恐怖类型的电影是有一定市场的,而且“失魂”的本土味也很浓。
青年阿川的身体里“住进”了别的人,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命案。
不过,导演显然没有要像通常类型片的处理方式那样简而化之——失魂是因为某种恶,杀人也是因为恶,恶被除掉一切就恢复正常了,而恶本身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或设定——不仅要说明失魂的来龙去脉,更重要的还要解释如何来“回魂”。
故事以父子关系为线索展开,“人”本身依然是被关注的核心。
人面临各种压力,有时候情况特殊,例如永恒又特殊的死亡的影响,人就可能失控。
至于如何被拯救,关键还是在“人”自己。
导演讲了一个“三个猎人”的寓言性质故事,局面就更复杂了一些。
在影片开始不久,生病的阿川被同事送回老家,途中有个有趣的细节。
纳豆扮演的同事在路途中抱怨。
他本不在护送之列,但因为觉得“台北很闷,要出来透透气”而搭上了便车。
结果却是:风景看一会就腻了,而原本期待的所谓“乡土风情”也没有看到。
又因为多了他一个,狭小的车内空间更加局促了,搞得大家都更难受。
充满幻想的城里人,到了城外后,失望了。
精神心理疾病常会被贴上时代性标签,和城市一起成为现代性的特征。
远离城市,是否能够远离烦恼呢?
回到家庭,是否就能找回失去的魂呢?
给出了“回归”设定的导演又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或者说事情没这么简单。
阿川是个厨师,干的是杀生的活,非常频繁地接触死亡,这是阿川发病的直接诱因。
因为关于死亡,阿川偏偏是个敏感者,他有童年时挥之不去的阴影:他看到父亲杀死了母亲。
他见证了死亡,不仅要承受失去母亲的不幸,他还要面对制造了死亡的父亲,太残酷了(阿川之后选择了或者说只能出走)。
按照父亲的说法,他是应身患绝症的母亲的请求而动手的。
不管父亲说的是不是真的,至少在那时无法化解阿川的压力与困扰。
阿川生病后被送回家回到父亲身边,有了重修“旧怨”的机会,但结未解之前,回到以前的环境对阿川反而是种刺激。
阿川更加失控了,他杀死了照顾他的姐姐。
而且失控的人也不只是阿川一人。
为了阿川,为了这个重新回到身边的儿子,父亲杀了来找女儿的女婿。
父亲陷入一种偏执,为了儿子做什么都在所不惜,不仅为过去,更为了将来。
但未来会怎样,他其实也不知道,但他能做的就是守着儿子。
带他看病;面对威胁也不会手软。
影片的核心——“三个猎人”的故事——本身并不难理解。
看着危险还带有死亡气息的带枪猎人,不仅于“我”无害,还在遇到困难阻碍的时候,帮“我”脱困。
要解决问题首先要克服恐惧面对问题。
对失魂者阿川来说,就是要直面让他失魂的根本原因:童年时目睹父亲杀母。
克服现在的恐惧,才可能拯救那个在那时候就压抑迷失堕入黑暗的小男孩。
不能再逃避了,黑暗的种子已经萌芽,再这样下去就只有毁灭了。
故事里的三个猎人,对应到阿川身上又是谁呢,帮助阿川的人在哪里?
因为“三个猎人”有明确的“三”这一数目,所以很明显,在电影中对应的就是被杀死的姐姐、姐夫以及警察三人。
杀死姐姐让阿川某种程度上处在了和父亲当年的一样的状态:杀死至亲但其实并没有来自本人(杀人者)的恶意(父亲是帮母亲解脱,而阿川则是“生病”了)。
之后父亲杀死来寻找女儿的女婿,就有明确的目的了,那就是要保护阿川。
来自父亲的爱,阿川显然也感受到了。
他主动要求继续“关”在小屋里,以免继续失控给父亲添麻烦。
最后阿川杀死闯入者警察,就不是失控了,而是一种自我保护,为自己也为父亲。
这时父子两人因为闯入者已完全处于同一阵线。
父子之间的误会消除了,阿川的病肯定将会好转,而父亲也终于得到了解脱。
三个死者,也是三个使者,引领着失魂者阿川,走过生命中最黑暗的一段路,回到正途。
“三个猎人”在心理逻辑上可以自洽,但在情节的具体体现上或许会有些问题。
被杀死的人都是无辜者,用别人的死亡来拯救自己,旁观者(观众)总会觉得变扭。
或许这也就是影片很凌厉深入,但却有点无法真实触人心弦的一个原因。
人物,不管是主角,还是那些牺牲者,多少都有些符号化,这或许也是“类型化”一个弊端。
除了父子二人,影片中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值得一说。
那就是梁赫群扮演的在地警察。
他也是阿川的同学,在阿川离家之时他常看望照顾阿川父亲,代了阿川的子职。
阿川回归、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他也没有要对付阿川(自己危险时也没杀他),最后还遵照阿川父亲的意愿处理后事。
梁赫群这个容易被忽视的人物,其实在整个电影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故事及主题提供了不可缺少的中介与补充。。
他身上有导演赋予的双重身份:他既是可以信赖的“家庭成员”,又是一名有公职在身的警察。
这样的特殊性,让他成为外界可以进入到失控父子世界的唯一人(女儿女婿是身份弱势,外来的警察是情感弱势,都是单一性的。
)。
他也不仅仅是一种联系而已,他进入其中,在这对父子其中一方缺失时,在一定程度上充当其角色,维持适度的生活秩序,使这个失控的世界不至于完全崩塌,并有了恢复“正常”的机会。
《失魂》是部有质量的又很特别的惊悚心理片,在表演、艺术性等方面也很有特色(本文主要就“失魂回魂”尝试解读,其他就不多展开了)。
而《失魂》跟钟孟宏导演之前的电影相比,对一般观众来说,会有不小的落差,口碑也有些呈两极化。
不过,导演似乎没有要停止在电影商业化类型化方面的尝试,下一部电影《一路顺风》将更加通俗化。
那会是怎样的一个新局面?
8 ) 失魂,少年与成年的一次扑救
剧情阐述阿川晕倒回家疗养,将自己姐姐杀掉,父亲隐瞒,并得知阿川此时已经不认识他。
后女婿来寻怕被拆穿父亲将女婿杀掉。
期间两人一直居住在山上。
后警察注意到派人来寻,被阿川杀掉,发小最后本可以杀掉阿川但是念在他父亲的情谊上留手,并同意了阿川父亲的计划,拿阿川父亲顶罪。
阿川始终提及自己是另一个人的灵魂,这可能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父亲将母亲杀死被他看到,后来外地工作很少与父亲联系,以至于父亲以为这个儿子不存在。
他时常做梦看见无关的人,跳入奇怪的井,看到母亲和“阿川”,以及三个搭车的猎人故事。
父亲应当也是拥有些心理疾病,从安眠药可以看出,儿子很少联系他,几乎不存在,妻子早逝甚至是自己帮助的。
通过影片我具体提出以下四点问题。
1.姐姐的死作何解释?
心理应激反应,可能受父亲影响,最亲的人也会持刀相向。
2.猎人的故事有没有隐喻?
小时候的阿川又做何解释?
梦里是他先帮助了三个猎人,三个猎人又反过来帮助他理清了山体滑坡避免了他被困,继而遇到小阿川。
可能隐喻为小阿川因为小时候的事情困惑混沌,犹如困在了山里。
而长大后的阿川帮助小阿川走出这一深山,因为有前面事的发生才会有结尾阿川的补述。
3.梦里出现的三个奇怪的猎人是否可以隐喻为父亲、警察、发小。
其实可以,三个奇怪的猎人对他本来就具有威胁,如果从“非阿川的灵魂”角度来看,这三个本就是陌生人。
如果从阿川角度来看,放在现实里,父亲具有疏远距离,警察定他罪,发小又许久未见。
但其实有些牵强。
4.父亲是否有心理疾病?
父亲同样介怀儿子看到他杀害妻子。
同时他看到儿子杀害亲姐姐的现实可以类比与之前他杀害妻子,两人的信任已经处于一种崩塌,所以他会做梦儿子埋他。
结,父子俩人已经形同陌路,牵连的唯有那身上的血脉和名义上的父亲。
最后父亲替罪是对儿子的一次补救,也是阿川最后走出雾霾的关键原因。
可能他已经认识到母亲的死的真相。
9 ) 贪婪的停驻…
贪婪的停驻…故事叫做失魂,自己看到的是夺魂,是的,停驻在本不属于自己的躯体之内,索求无度,奈何还遇到一个为自己不断善后的父亲,这个故事注定滑向不可知的疯狂境地…时而清醒,时而混乱,毫无逻辑的行为之下却又处处让自己可以存活下去,所以,也许幽魂只不过是一种媒介,一种让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存在的渠道…总的来说,虽然肉体是一个躯壳,但是理所应当的占据了别人的躯体却又丝毫不觉得抱歉,这样的灵魂哪里值得救赎呢,奈何遇到的是一个可以无怨无悔身体力行的去为其善后的父亲,所以,比之男主的行为,自己觉得父亲的行为更加癫狂,这种沉着克制之下的癫狂让人不寒而栗,个人评分8.1分,推荐指数四星。
10 ) 一部假的恐怖片!
靠!
我惊呆了。
最近最大的惊喜。
这是一部打着恐怖片外核的实际上描述伟大父爱的绝绝对对被低估了的片子。
他用极端的难以想象的方式保护了他的儿子,扭转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尽管你还是感到由衷的悲哀。
钟孟宏玩得太精了,逻辑前后完全自洽,把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外化得特别好,你以为的离奇一点不离奇,最后儿子的魂被老父亲的爱召回了。
间中惊人效果中端出十足的幽默。
台湾这帮演员有一套成熟的有说服力的表演体系,看似一本正经又自然不留痕迹。
每个角色都很耐看。
张孝全真是帅。
一部从头到尾引人投入的片子就是极好的。
为什么那么多人没看懂?
山林欲动,山林静止,虫鸣声,我屏住了呼吸。
好想让AM看这部片子啊,他肯定会喜欢的,应该可以治愈他。
开头那首《青春小鸟》的变调也是神笔。
钟孟宏是目前把暴力和诗结合得最好的华语导演,想研究下他的脑回路,他洞察人性最深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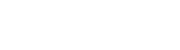

































220801回顾 特殊的魅力。摄影,表演都比较喜欢。
真是装得一手好逼,内容却是渣得一摊好屎。电影的意识形态做得很足,气氛营造到位了,但故事和想要表达的都没讲好。多多少少有些没太看懂。废话,这么讲故事这么绕谁能看得懂啊。
以为是恐怖片,看的有点失落,却在片尾发现是真事改编?
男孩抱着妈妈哭泣的一幕让人心碎,看似麻木的人是不是心里都住着深深的悲伤?
看到半夜没看懂。。。。。。。。。。。
其实就是一部犯罪片,但是却拍得很煽情,杀妻(助其安乐死),杀女,杀女婿,杀警官。这是犯罪,与亲情无关。
原来那三个猎人就是女儿女婿和杨警官 带他们一程 才找回了儿子 这文本确实高啊
就想问一句 张孝全 你很缺钱吗?
兩個神經病,一個比一個更有病
★看不懂的电影就是烂片,哪怕再文艺,而且剧情太平静。
看得心累
不知道想表达什么。打工青年麻木冷血赛过杀人犯?连父亲都不认?
去找寻那个不再回来的儿子,而当初,是他造成了他的离开。而收留那个漂泊的灵魂的人,就是这个假的儿子。所以原来,是他救了他啊。这个父亲,会不会能够意识到哪怕一点。
因失爱而失魂,精分迷题晦涩,对白生硬冷洌,山林气氛诡异奇美。全然不顾观众感受的惊悚文艺片。
故事都讲不好还想弄个意识流 整部电影故弄玄乎 里面没有一个正常人 台词 演技 尴尬出戏 剪辑也乱七八糟
画面美 摄影好 气氛营造得好
大半夜因为张孝全犯花痴😂😂😂
完全看不懂
钟孟宏的风格一直那么独特,雨后浓雾的山林,长满青苔的污水池,还有没有底的井,木屋洒满血迹的窗口,算不上是一部恐怖片,倒是颗内心甜美的苦瓜味软糖。
整件事情发展下来好像理所应当的,空镜头的插入,再加上灵异元素的涉及,但到故事结束发现,事情并没有真的结束,仅仅是结束了表面上的一切,而内核却未触及,或者说从电影开始,内核就没触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