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灵之马》剧情介绍
“1889年1月3日,都灵。弗里德里克·尼采在维亚·卡罗·艾尔波特酒店的六号门前驻足。他的目光被酒店外的一个马车吸引。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小马车。马车的车夫遭遇到了一匹倔强的马。不管车夫怎么喊叫,马匹根本没有要移动的意思。最终,车夫失去了耐心,拿起了鞭子,朝马匹打去。尼采见到此番情景,挤进人群,冲到马匹跟前,阻止住马夫,抱住马的脖子,痛哭起来。酒店的主人赶来,拉走了尼采。回到酒店的尼采在沙发上安安静静地、一动不动地躺了两天。随后,他小声地说了几句话。接下来,就是尼采精神错乱、神经颠颠的十年,由他的妹妹和母亲照顾的日子。谁也不知道,在都灵,在那匹马的身上,在尼采的心理,发生了什么。”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羊年喜羊羊黎明舞影随行海神号当我望向你的时候黄金罗盘青年莎士比亚少年远游她的重生鳕鱼角第二季贱神三少爷2我的妹妹哪有这么可爱第二季恋爱好烦,不如结婚吧!蜜恋失心嵩山武僧真红之星动物学迷恋雪山惊魂血战江城爱情场景编号血量子蓝调天后安昙春子下落不明秋丰满月时孔雀镇午夜死亡2课后狂屠第28年的甲子园你想沦陷于我
《都灵之马》长篇影评
1 ) 贝拉塔尔的残酷世界观
我们抛开那些关于电影节还有收山作那些花边新闻,深入到电影文本来斟酌这部伟大的作品(或者贝拉塔尔每一部电影都可以看做是伟大的)。
电影唯一与尼采的联系就是开篇那段话,由此本来一匹普通的马成为了那匹导致尼采彻底疯癫的传奇之马。
本来一个具有普世寓言功能的文本,却偏偏要与尼采联系起来而具有某种传奇性。
那么文本必然与尼采的哲学理念具有某种隐秘的联系。
这种联系最为清晰的表露在那个外来人,那个胖叔叔讲了电影中最大的一段话,估计比其他所有人在整部电影中说的话都多。
这段有明显“查拉图斯特拉”倾向的独白(“上帝已死”的含义跃然纸上),却被马夫(片中的独臂老人,也是一位父亲)以一句“瞎胡扯”为终结,从某种程度而言,贝拉塔尔借助主人公传达了一种“反尼采”的倾向。
但这种“反尼采”并非指向尼采“反基督”的哲学观点,而是通过父女两人在六天的生活来反对尼采晚期引以为傲的“超人哲学”---期望成为超越理性,超越自我,而重新实现自我评估和自我升华的“超人”,这种充满精英意识的哲学理念在面对严酷的生活的时刻,显得那么浮夸和形而上学。
或许在卡罗·阿尔伯托广场的尼采看到了这匹马的未来,看到了都灵之马和马夫女儿面对死亡却维护一种生命的尊严,从而彻底否定了尼采的“主人-奴隶道德观”。
上帝用六天来创造世界,第一天上帝创造了光,电影中第五天光消失了,第二天创造了水,电影第四天水消失了。
这种“反创世纪”的过程,预示了第六天的父女已经陷入到一种混沌的“死”的境界,正如第五天最后,导演的旁白已经叙述了“死亡已经沉落”。
在这种“死”的境界中,父亲仍然啃着生的马铃薯,还要求女儿吃,就如同女儿要求那匹老马进食一样,这是在死中仍然坚持生命的体现,这就是贝拉塔尔最为朴素却最为残酷的世界观。
2 ) 上帝又死一次?
上帝用六天创造了世界,贝拉塔尔用了六天逆向了创造过程,没有光,没有水,即将死去的马,昼夜不分混沌的暴风天和终于沉默不动的人们。
写下上帝已死的尼采和都灵之马一起走向了终点。
尼采说上帝已死,但上帝其实早就死了,根本轮不到尼采来宣布。
从15世纪的文艺复兴到17世纪的启蒙运动,人已经完成了祛魅,实现了理性主义和主体性,在人本主义、现代性和科学的光芒中埋葬了上帝的宗教世界,人才是万物的尺度。
到尼采生活的19世纪,离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都已经两百年了,那时科技昌盛,埃菲尔铁塔都造好了,中世纪宗教的余灰早已无法影响世俗世界,这时候尼采又再次宣布上帝已死,难道是在鞭尸吗?
不尽然,因为神创论追寻人之上的上帝,与现代性探求世间万物背后普遍性统一的科学法则,在根源上是相通的,都可归结为求索柏拉图哲学中现实世界之外的形而上理念世界。
尼采要颠覆的不仅是上帝,更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包括理性和现代性世界,一切价值都要被打破,都要重估。
尼采之后都已经是后现代性了,宗教思想那都是几百年的尘封往事了,其实尼采和上帝早已没什么纠葛了。
3 ) 都灵之马:尼采的壳,塔尔的魂
一开始通过简介加上塔尔一贯冷峻压抑的风格,本以为会是部相当复杂晦涩深不可测的电影,看过后仅通过视觉传达的信息来看,无论是局限的空间、简易的场景、稀少的对白,还是单一的人物,毫无情节的剧情,都显得那般的简单和明了,但从中所折射出来的哲思深度和寓意的含义却又显得异常的深邃和高超,在我看来,塔尔不单单是要找出尼采的病因或刻画他寻常的生活这么简单,而是要追溯和探讨其背后强大而根本的哲学原由。
摄影依旧延续着塔尔钟爱的黑白色调,不但造就了一个不被干扰的纯粹空间,同时这种复古原始的画面感正好能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找到一种很恰当的契合点,加上透着忧伤、悲怆和哀怨的美妙配乐,使得整部电影的氛围显得异常的沉重和凄美,而蕴藏其中的却只有两父女日复一日在有限的场景中看似枯燥乏味重复的过日子,但通过塔尔对于镜头冷静独到的掌控和捕捉,像是一个固定镜头的长时间静止停顿,或许在有些人看来会显得极其的烦闷和无聊,但看完后就会发觉塔尔的构思其实是相当精妙和天才的。
塔尔可以说在一个看似简易的布局中打造出了一种精密复杂的哲学架构,通过父女俩平淡寻常的日常生活和自然的微妙变化,以及对于镜头一流的运用和诗意的表达,来反应自然、宗教和个人在哲学意义上的存在价值,就像本片的起因是建立在日后尼采因一起看似普通的事件而引发的精神失常一样,在我看来尼采的身份和经历更像是塔尔为筹划这部杰作所借鉴的蓝本和选择的捷径,无论是尼采本身,还是《都灵之马》,都是从浅入深透过平凡的常态获得一定思想上的升华,或许在平淡普遍的意向中真能体会到一种酷似返璞归真般最为本质的深刻顿悟。
整部电影由时间划分为几个小段,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不厌其烦的重复着生活中的日常和琐碎事情,但在整个看似索然无味的过程中塔尔却很精妙的融入了些许变化和外来因素的入侵,从马的强烈反感和失控,买酒人神乎其神的倾诉,一群自由享乐派的吉普赛人,突然干涸见底的水井,奄奄一息萎靡不振的马儿,怎么点也点不燃的煤油灯,到最后只能无奈的生吃硬邦邦的马铃薯,通过这些别具匠心的设计和越演越烈的变化,可以很微妙的感受到一种自然与生物、人类与动物、社会与人类间的某种无形而紧密的联系。
强势的寒风在外肆意嚣张的搜刮和攻击,变化无常的大自然所爆发出来的强大能量,让一切在其面前都显得无比的渺小和卑微,马变垂危,开始缺水,没法搬家,只能寸步难行的坐以待毙,那一刻脆弱的生物在气势磅礴的大自然面前是何等的微不足道不堪一击。
从不修边幅憔悴不堪的表外可以窥见到以往马儿整日奔波劳累的情形,一个是身份等级的不公划分在人类和动物的相处模式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另一个是从马儿的情绪表达和最后的身心状态中,仿佛能获得一种只能在被动、束缚和无奈的生存条件下痛苦活着的强烈而悲观的共鸣,这点通过尼采的遭遇似乎能得到一定的理解。
除了父女俩,纵观全片就来了两路人,通过他们的言语和行为可以发现两个共同点,一个是传达出对于宗教信仰的质疑,另一个可以把他们看作成一种外来文化和思想风潮的入侵,个人与社会间的相互联系,当强势刻板执意要拒绝融入或接受当代文明或思想,想要完全忠于自我存在时,从最后那个透着无限苦涩和悲哀的镜头可以看出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当因主观强硬的自我意识或遭受外来影响没法挣扎和反抗的陷入重重危机之中,当上帝踏入冰冷的坟墓信仰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空谈,当塔尔打造出以上所有令人绝望的条件时,在看似不断消失和逝去的过程中,反而是一步步回到了最初的原点,反应出生存的必然与本质。
4 ) 当我们的生活被鲸鱼和马匹所笼罩
当我们的生活被鲸鱼和马匹所笼罩创造一种场域,便有着一种权力蕴含在其中,而这种创造性的权力的运行势必就会带来一种理解世界的态度,(即叙述与电影的呈现方式)。
也就是说,创造一个场域,便是创造一种理解的可能性。
再过去的历史当中,交给我们人类理解的对象是上帝一或者说是命运,而如今这个时代留给我们人类去理解的终极对象,或者说在我们这个上帝缺席的存在主义时代理解成为了个人性的命题。
而在这两部电影中(《都灵之马》和《鲸鱼马戏团》),鲸鱼与那风作为上帝的化身再度降临到了世间。
所以在贝拉他而所创造的场域中的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反抗变得更为复杂和忧郁了。
要想进入这一个个导演所营造出来的电影场域当中,我们势必需要一种手段,也就是一种途径。
这种途径要求我们去在一个拥有与之相等的力的作用下去进行“观看”这种行为。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种可以与电影中导演所创造的场域所相等大的反作用力。
也就是说这种场域的力越强的电影越需要我们投之以越强的力。
在黑暗的绝对中去同强有力的观众一起相汇聚并营造出一种专注和进入的能量,来去投射向吞噬一切的银幕———这便是我们创造这种反作用力的办法。
只有当电影中的力与观众的反作用力同时存在且大小相同的时候“观看”与“接受”的这种行为才能够得到平衡。
这两部电影的场域之力都极其的强大,对于电影院是最合法的观看方式。
《都灵之马》中:凝视与专注的长镜头,命运的旋律,极度规律的琐碎日常,极为统一的视听语言。
这一切让这部电影的各个层面游走于“一切的意义”与“无所是”之间。
这是一场“一切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的巨大的疯狂的崩溃的无情事件”。
《都灵之马》就好比一种《鲸鱼马戏团》的延续(果不其然“一个伟大的导演一生只拍一部电影”)在这两部电影的世界中的动物无一例外的都打破了剧中人物生活的绝对惯性,在《都灵之马》中是那“木虫”和那“马匹”,而在《鲸鱼马戏团》中则是那只绝对大的“鲸鱼”。
而这些动物往往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不可知的真相感。
这些动物是上帝纯洁的创造品,他们或许比我们更接近上帝。
而这些上帝的造物带给我们的便是一种笼罩在我们上方的一种不可能性。
在《都灵之马》中,这种“上帝七天灭世”的源头在于人类的“大堕落”。
而对于《鲸鱼马戏团》来说,那场运动的源头则是一种巨大的悲壮的无以名之的无力的反抗之愤火。
在后者中,当小镇上的人去试图抵抗,去进行革命运动后,最终我们所得到的所看到的在那个帘子后面的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饥瘦赢弱的老人的骨体,我们得到的不是新生的希望,而是疾病般的绝望。
“王子”就好比像是大卫林奇电影中经常出现的红房子里面的老者一样,他可以是这个世界背后阴谋论般的主宰者,又或者是一个上帝的遗臭—诉说着一种不可能性。
这个不可能在过去的时代里更多的表现为人类理解命运的不可能,而在近代则表现为人与人理解的不可能。
同时,在一切的历史中,所有的一切都表明我们的历史就是个闭环,我们的世界就是个闭环,这个世界不会好到哪去,也不会坏到哪去,他只会让人想要去反抗,然后随之绝望。
我们已经看完这部讲述一切的反抗和随之而来的绝望的电影了,我们观众反抗贝拉塔尔的企图变得更彻底的绝望了。
5 ) 沒有結構或者沒有生命
電影是有節奏的。
其實文字也可以是有節奏的,不只是小說裏情節的變化和鋪排,而是在描繪一件事時,文字的祥略、推進的快慢,都可以營造節奏。
故事的好壞,內涵的高低是一會事,而節奏的把握對寫作者來說,可能就是手藝精湛與否的體現。
這是我自己的解讀,而我以前認識一位80後作家,她的說法是,小說的關鍵在於結構。
我想一個故事整體的節奏是什麽?
就是結構。
那個作家她成名之時文字華麗,能文言能白話,辭藻浮華,盡顯家學深厚的功底,到了她大學快畢業時,文字反而樸素得和網絡小說差不多了,這個時候,她說小說的生命是結構。
而也有人說過,一首歌的好壞是看旋律,但成敗又在編曲的結構。
現在若還把文學和電影做比,似乎已經落後了幾十年,何况貝拉塔爾師承的,不就是宣告文學和電影决裂的塔可夫斯基么?
是的,電影和文學是兩碼事,但我卻忍不住覺得《都靈老馬》的長鏡頭,是文學性的長鏡頭。
你可以說老貝的鏡頭運動如詩,那麽如果把文字和鏡頭做類比,《都靈老馬》的鏡頭一方面看上去繁復而淩厲,但又直接準確。
但早把長鏡頭玩得爛熟的老貝封筆之作最值得稱道的可不是“文字”如何絢麗,甚至我不想去贊美導演的staging,或是電影漫長鏡頭中閃光的細節,那些留給别人去贊美吧,在這裏我只想爲簡單而精妙的結構鼓掌。
電影內容五味雜陳,故事卻很簡單。
讓尼采痛哭的老馬和馬夫回家後6天的生活,第一天,描述馬夫和女兒一日平常的生活,女兒在家,每日去屋外的井裏打水,準備晚飯,一成不變的全是煮土豆,馬夫則應驅馬出外工作。
但自第二日起,父女兩人不斷遭遇不幸,屋外的颶風已令荒原小屋有如孤島,而老馬突然不願再拉車,甚至不吃不喝,馬夫便不再出門工作。
第三日一班吉普賽人路過,不問自取的喝了井水惹惱了馬夫。
次日井水莫名其妙的就干涸見底了。
之後馬夫收拾細軟帶上老馬打算搬離此地,卻走不過一個山頭就折返而回,到了晚上,連油燈也不知爲何無法點燃。
到了第六日,父女原本規律的生活已經被破壞殆盡,父親一切如常,吃著碗裏的生土豆,對沉默不語的女兒說“你必鬚得吃。
”這正是女兒對絕食的老馬曾說過的話。
電影到這裏結束。
第七日會怎樣?
不幸會繼續奪走父女所擁有的平凡生活?
父女會堅守在家園直到連生土豆也沒有?
還是第七日便已到世界末日?
這個描述人類生存之道的絕望故事,簡單而讓人回味。
簡單的故事往往能包含無窮的道理,尤其是在人類似乎快要末日臨頭的當下看來,更是震撼人心。
說回結構,我相信電影藝術的好壞不在故事如何,而是如何說故事。
《都靈老馬》分章節而成,如同樂章般,原本的節奏便是父女倆曾十幾年如一日的生活,電影中的六日,兩人每日都欲重復同樣的節奏,但各種“不幸”卻化作變奏漸次加入其中。
父女面對變化卻沒有太多變通之法,唯有堅持如常的生存之法。
這種重復中變奏,變奏後又見不變,從而反襯出主軸,這樣的結構,印象在許多小說中都能見到,但這又像是音樂中常用的技巧。
道理似乎簡單,但如何在結構中巧妙而合理的安排,又是看得明白不易做到。
老貝不斷重復的描寫父女兩重復的生活,但隨著故事的變化,鏡頭的節奏也在變化著。
比如女兒之前打水時,鏡頭都會跟隨前往(但是是不同的角度),路程顯得艱難而漫長。
而在井水干涸的那個早上,鏡頭待在門裏,看著女兒走到遠處的景邊,再到女兒回來緊張的叫上父親,鏡頭才又跟著兩人到井邊,但隨著兩人焦急的步伐,鏡頭的移動速度已和前面不同,快了許多。
就這樣一個景别和一個速度的變化,就完成了情節到電影語言上變奏的同步。
而電影中看似冗長的鏡頭裏還包含有眾多細節——絕計不只是驚人的鏡頭移動——恐怕并不是看一次就能將他們完全捕捉到的。
我只能體會到大的結構,在回味中大致體會出許多細節的精彩之處,但恐怕仍未能及其深意。
相信無論是情節推進抑或鏡頭安排,都是貝拉塔爾花三年時間,殚精竭虑造就,更何况故事寓意無窮,以極簡及極深,難怪貝拉塔爾將這看作他最後一部作品,因爲他要說的,都已經說完了。
——————————————一如往常的貝拉塔爾,影片的第一個鏡頭總是能夠讓所有人———哪怕是半小時後就會睡過去的觀衆拍手叫好。
他的黑白攝影也好得完全不像是同時代的人。
想想之前在文化中心看的《鬼子來了》,雖然姜文也是拿去歐洲沖洗,但是這個黑白啊⋯⋯和貝拉塔爾拍的真是差一截,究竟是爲什麼咧!?
影片有一處讓我無法不走神的地方,就是那個說最多對白的胖子,那個緩慢的zoom in實在讓人昏昏欲睡⋯⋯這麼直接的對白似乎也失掉了影像之美,何況⋯⋯這冗長的對白並不直白易懂。
另外,第一個長鏡頭中凌厲的配樂絕對是讓人印象深刻的,但幾乎完全沒有變化的在不同的情況下不斷重複使用——並沒有讀懂每一次音樂擺放的用意,但這激烈的旋律到後來實在讓我有些抗拒了。
6 ) 尼采与马的对视,西西弗斯推着石头。
#Curzon#二刷 25082024 跟一刷时候的感受差不多,贝拉塔尔的灭世,荒诞的生活如同西西弗斯,西西弗斯是否幸福取决于他是否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接纳它。
#MUBI#一刷 07072022 开场电影引用了一个小故事,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部分,第一,哲学家尼采抱住一匹被虐打的马啜泣并发疯,第二,发生的地点“Not far from him(现场的马), or indeed very far removed from him(父女所在地)”。
接着一个老者赶着一匹马在狂风之中前行作为定场镜头,展现出一种“生活”。
我认为整部电影与开场尼采的关联性在于,这个老者和他女儿所代表的是尼采抱住的“马”,而无情虐打马的马夫则对应着大环境,那狂风,那枯井,那生活。
而尼采这个表达出“上帝已死”言论的哲学家似乎就像是拥有上帝视角般的观众,来看着这对父女在经受苦难却无所作为也无能为力,只能啜泣。
太喜欢第五天和那匹马对视的镜头了,似乎一个轮回,静静的对峙,我们代表着尼采,看到它的苦难,似乎在想理解它的想法,就如同它就是这对父女,是我,是都灵之马。
镜头上,面对“虐打”观众无法逃避这个由多个长镜头组成的“上帝视角”,大提琴和管风琴的配乐响起则会让这冷峻且现实主义感极强的长镜头充满存在主义气息。
室外迎风前行多采用中全景或中景低机位仰拍,让人物占比更多,应该显得有力量,但搭配狂风的音效,和营造出的狂风,从视觉和听觉上放大了自然的力量,让人物在其面前如脆弱的蝼蚁。
影片也大量使用空镜,来展现环境的恶劣程度。
构图上,影片的构图更是多利用窗框或门框将黑暗的房间和明亮的室外做隔离,让人物压缩在重构的狭小的空间中。
还有室内吃土豆的对称构图,即使重复在多次也不会觉得突兀,甚至在最后一个镜头我都要哭出来了。
到结尾,上帝如果用6天创世,那贝拉塔尔则用了155分钟分“6天”毁灭了世界,在毁灭前,让我们感受到人(母亲)的消失,牲畜(马不食)消失,水(被偷)消失,昼夜(一片黑暗)消失,光(火烧尽)消失,世界消失。
而面对消失的一切,依然要“吃土豆”。
7 ) 肉食性影迷对草食类大师的告别
作为最广食的食物链顶端,人类天然有独一无二的自我毁灭体质以平衡自然生态:我们天然喜欢有害自身健康的食物——全世界的小孩不分种族性别都偏好烂牙的甜冷零嘴,蚀钙的碳酸饮料,高热的油炸嘴。
经过后天的训练有些人能克制甚至进一步遗忘这自虐的乐趣。
可惜那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人,倡导素食长寿的健康专家们痛心疾首。
幸好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至今热爱冰淇淋,巧克力和红肉的某只举臂欢呼。
不明真相的普通观众如果误入这位去年封镜的“大师”或者前不久才过世的安哲,根本是饿了三天的食客被领进一家菜单上只有低低盐生菜沙拉和青菜豆腐的素食店——连人造有机蛋白都不提供的哟,亲!
无论那些小部分的人用怎样的营养搭配或者味觉原理循循善诱“这其实是很好吃的哟,亲。
你多来吃几次就习惯了,就能体味出个中美味了”,自小乖张的姐几乎每次都横眉怒目掀桌踹椅——要姐特么吃这些东西,人生还有何乐趣,不如去跳海罢!
买书之前我们可以在书店翻阅全本,买CD之前我们可以在音像铺听取每首曲子的片段,去博物馆之前我们可以在网上或者目录里浏览展品的片,即使是音乐会体育比赛舞台剧这些现场节目,观众至少也可以用嘘声羞辱表演者以补偿自己损失在无趣表演上的金钱与时间,电视的话几个有线台全年才收一点费用节目还多样。
唯有电影观众是最弱势的,毫无还击之力。
即使在网上吐点不满,都有各种圣母君跳出来哭泣。
所以姐以为端个小凳子在这些被那些自称营养专家的家伙吹捧上天的店面门口挥春一张“肉食者免入”是吾辈“非典型影评人”(称“非典型”因为姐自认不是,也并不以此为生,但在某些同学的定义里姐也算是边缘人)的职责,一则是让吾辈浪费掉的票价和时间多少有些意义,二则是观影界这种专以违反天性为美的歪风需被顶上一顶。
作为以清淡江浙菜养大的南方人,姐进川则日日红锅,北上则天天酒肉,都磕得入味,自认已经对食物的包容性已经算普通人里偏高的。
虽然要试了几次非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才把《伦敦来的男人》坚持看完,但是之后还是多少有些乐趣——几天之后姐特么的还能在脑内从头到尾播放这部电影,长镜头如何移动怎样角度,镜头与镜头之间如何衔接,哪个场景配乐了哪个没有,全都清晰明了,甚至可以随意定格,从记忆里截取出这一格的画面,光影历历。
也算符合“极简”的审美,呈现出来的线条的确简单,但每根线之后的思量准备功夫还可以玩味。
所以姐常常自视过高,以为啥都咽得下去。
明明心里有张黑名单的,有时出于好奇心,有时碍于时间表,有时是被某一部影片所激励对自我的口味产生了极大的误会——比如这次就是从《伦敦来的男人》里得到画面逻辑的乐趣,就完全不记得当年看《撒旦的探戈》时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居然兴冲冲的想尽办法硬排时间去看这部封山之作。
这片甚至没有《伦》的干净明确。
姐有另一种自虐的倾向,就是无论多无聊,只要还在能撑住的底线以上就会坚持看完。
实在注意力涣散了就四下数看看有多少观众已经睡着了,然后以我数的次数和观众睡着的人次为反比打分。
能在Le Clef这种艺术院线里把专程闻名而来的法国观众弄到东倒西歪,这种威力如果尚未见识过又有好奇心的同学可以领教一下试试看。
故事以尼采发疯的传说为开始就有种大妙的预兆——据载尼采某天出门遛转的时候看到路旁有一农夫在鞭打一匹不肯前进的马,上去抱住那匹马大叫“我苦命的兄弟”(之类的),回去之后说出了那句名言“老妈,我想我是神经了”。
之后关于尼采的人生反正在江湖上广为流传,但是那匹马的命运如何泥……好吧,这多少还是有点悬疑的。
然后的塔式长镜因为有心理准备倒在承受范围内。
从马出场,到切到马夫,拉开到远景,移拍出马驶入浓雾(根据塔式传统雾就是“故事从此开始”的标志,隔开现实和孤绝世界的分界),马车停到农舍前,女儿出来帮助卸马具,镜头然后跟女儿进入马厩,再转到农夫推车入内,这一段的人物和环境关系介绍还是有《伦》一片里的清晰感,姐自以为终于能欣赏“大师”了有木有。
之后必须杯具啊有木有!!!
在其他艺术类界,比如古典音乐类,莫扎特的作品未必人人听得欢畅,但至少大部分人亦不会生出“这是座头鲸星来的外星人写的么?
”这样的频谱不谐感,即使不是红烧肉油爆虾,至少是清蒸鱼白灼虾。
而《月光下的皮埃尔》无疑是需要听众先学习一些低频鲸类的语言才能对得上号。
但古典乐迷鲜少有人称勋伯格比莫扎特“大师”——理由是前者更难懂和更违反人类的天然听觉。
绘画界也没多少人敢说某位后现代主义画家超越达芬奇。
但在文艺片这一领域里,被推崇为大师往往是以屠杀普通观众的观影乐趣为主要标志的啊!
上帝用六天创造了世界(第七天果断休息了),塔尔用六天毁灭了世界——还有姐对“大师”们的所有兴趣。
两个多小时啊!
姐其间不停在想——为毛我要看这片?
为毛?!
这一切是为毛?!
究竟是为毛?!!
好嘛。
每天老爹在女儿的帮忙下穿衣服换衣服的情节是对照女儿套马的场景,以人比牲畜。
第一夜照出房间里空的鸟笼,道出昆虫的寂静,其后几天依次抹掉上帝六天内创出来的世界——尼采名言“上帝已死”有木有。
农夫和女儿每天早上饮酒,酒即圣灵。
从山上下来的秃头男是来沽酒的,该男带了一根拐杖——圣经有一节教人出门不要带拐,宗教也被称为“心灵的拐杖”(更别提秃头男说的那篇《查拉图斯特拉》语言风格的灭世预言)。
又从山上下来信仰依所居地而变化的吉普赛人,套着两匹白马——白马有一种解释是“敌基督者”,称农夫的女儿有“魔鬼的眼睛”,并叫嚣“土地和水都是我们的”,给农夫女儿留下了“圣地被玷污,必将灭去光”的新一轮灭世预言。
次日他们唯一的水源便干枯了。
农夫打算搬家,女儿取出母亲的遗照——故事中只有一匹马,一个左手残疾的鳏夫和他的独女,亚当和夏娃无法繁殖后代,连可被挪亚带上方舟的成双的动物都没有,是人类的灭绝。
在外面绕了一圈又从山上回来的农夫父女成为最后的灭世预言。
户外强劲的风是灭世的神力(秃头男称城镇都已被风刮倒)。
太阳消失。
风也平寂。
唯一剩下的光源是火。
查拉图斯特拉是祆教的先知,拜火教是最早的二元创世论宗教,所以当火种也熄灭(所以父女最后只能吃生食),就是世上再无善恶,重回混沌。
在两个小时里,要姐调动出各种记忆库才知道它在讲什么,这种东西有什么趣么!!!
塔尔大师的好处大概也就是OST向来很美(虽然每一部都只有两三支这样,大/低音提琴是指人,管风琴指信仰),画面也总是很有质感。
而且镜头真的非常节省,拍重复的场景都不会用同个角度(否则姐真的中途离场了),而且镜头从来不在轨道上做来回的移动,如果一个中景镜头定在那里,而人物活动到镜头外,观众就知道人物还会回来而且会沿回来的方向继续前进并发生事件,这种不做无意义剪接和多余移动的极简还是合姐审美的。
也只有这样了。
其他的,作为一个骨子里的肉食主义者,姐表示吃不出塞牙纤维的美味。
僅以此纪念这位曾经与姐相对无语十几个小时的大师。
如果这个世界上尽是您这种菜,姐果断会疯掉。
但假如从来没有您这样的菜,观众的餐盘也不够多样化太不健康——也许罢……
8 ) 《风的呼啸,人的末路》
一.独特的长镜头美学匈牙利这个国家的导演似乎都很喜欢使用长镜头,无论是米克洛什·杨索在《红军与白军》中运用长镜头调度不断变化战场上的主角,还是贝拉·塔尔在本片使用的长镜头营造出的一种永恒的绝望,其对于长镜头都有着很深刻的看法。
本片第一个镜头拍老人赶马车回家:悲壮且在后面重复出现的和弦乐搭配着长镜头调度,时而对准人,时而对准马。
该镜头不就相当于李白在《蜀道难》中开篇的一句“噫吁嚱”直接告诉观众我这是一部绝世佳作,需认真品味仔细体会。
本片通篇使用长镜头,两个半小时的电影用了三十个长镜头完成。
在长镜头中,框架构图形成景深(从屋子的窗往外看)。
但贝拉·塔尔的长镜头使用是来表现父女二人生活的无意义之处,在总共六天的日子里,叙事是重复的,重复的便是无意义的二.隔膜与陌路在本片中,各种元素都是有着隔膜的,都是远离的。
故事发生的小屋是与世隔绝的,强烈的风在不断吹打着屋子,换句话说,屋子与世界是隔离的。
同样的,人与人也是存在隔膜的。
作为主角的父女本该很熟悉有着许多交流,但在本片中却意外的并未有多少对白,甚至我们听到的第一句对白发生在影片的21分钟(“吃饭了”)。
这二人的疏离还体现在他们的距离感上:二者之间始终没有亲密动作,在无事之时总是隔得很远。
买酒人,坐在马车上的人与这对父女之间也隔着很远。
买酒人的末世言论不被父亲接受,另一批人被父亲驱赶。
人与人存在着距离。
当然人与动物也是疏离的,马在第二天拒绝外出,并在之后的日子里拒绝进食,甚至不给女儿面子。
不仅如此,就连最基本的人与物体,也似乎有着距离。
枯竭的井,吹不断的风,突然变暗的屋子,滚烫或冰冷的土豆,点不亮的油灯,他们与我们存在着隔膜与距离三.影片的存在主义倾向本片先是引入一个关于尼采的传闻之后开始讲述故事。
因为尼采对于意义,价值,存在的思考很深入,所以本片在开头便确立了其存在主义基调。
影片的剧情大多是日常琐事,且这些事不断重复(长镜头调度每次都不同):吃土豆,给马喂食,外出汲水,女儿给父亲穿衣。
这一切似乎并无存在主义的迹象,但他们的多次重复叠加却有了清晰的存在主义倾向。
因为重复,所以无价值;因为无价值,所以不存在;因为自身的存在无法得到认可,所以人物隔离、痛苦,陷入永恒的绝望。
这种痛苦无法承受,因为自身在意义上并不存在。
四.电影的警告电影圈有一句话“即使你能忍受《都灵之马》,那你也不一定能忍受生活”。
而生活之中的我们每天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他更加复杂而已。
由此看来,我们也陷入了无意义的怪圈,得不到自身存在性的认可。
我们似乎也会在明暗不定的房间里吃着冰冷僵硬土豆,在六天的时间里默默的重复着一切无意义的事情,最后无意义的死去。
本片虽处处有着长镜头美学,存在主义倾向,但他核心是在告诉我们人类的末路。
贝拉·塔尔在电影中似乎化身为了一位父亲,轻轻地、耐心地,甚至有些喋喋不休地告诉人类这个母亲,或者说是孩子 “妈妈我好傻”。
9 ) 关于《都灵之马》的几处辨析
以下设问来自于某老师,三年前觉得这几个问题有探讨的价值便尝试回答了一下。
一边感叹三年前文字真TM稚嫩,一边感叹自己当时真TM认真。
1.《都灵之马》中,土豆吃了几次?
几次吃土豆有不同吗?
一共吃了五次。
几乎是截然不同的。
第一次:从正面拍父亲吃土豆的细节,主功能为描述。
盘里的土豆的特写,摇到苍老的单只左手捏碎滚烫的土豆的特写,摇到满是胡髭的脸部吃滚烫土豆碎块的抽动的特写。
父亲的左手和左眼都有残疾,父亲吃土豆的样子饥饿、急切甚至慌张,不时抬起无神的眼睛看看女儿,一种被生活折磨到简单粗暴、渴望物质生活的个性。
第二次:过肩近景转为单人近景,主功能为描述。
女儿吃土豆平和、精致、若有所思,似乎在感受土豆带来的意义。
女儿身处周围的环境中并与之相容。
女儿是一种精神层面淡然的写照。
第三次:是从桌子侧面拍父女俩对称吃土豆的中景,主功能为描述和叙事。
在上两次吃土豆的基础之上表现人物关系,并置父亲的急迫和女儿的淡然,对比突出差异。
之后由父亲长时间的抬头看、女儿随之抬头看引出吉普赛人驾着马车来到的场景,吃土豆的戛然而止起着设置悬念的作用。
第四次:与第三次相反的角度拍对称中景,主功能为渲染气氛。
与第三次的构图十分相似,有趣的是这次父亲吃了半个土豆就坐在了窗前凝视窗外。
前一天井里的水干涸了,马绝食三天已经让父女俩深深忧虑,父亲的无食欲是他焦虑的外在表现。
同时,吃土豆这一举动已经被重复到使我们的感官疲劳,让人看到土豆就油然而生一种厌恶。
第五次:采取与第三次类似的角度,这一镜头是所有吃土豆场景中最长的,也是最暗的,沉沉的黑暗降临在头顶让人无法喘息,焦虑和绝望在几乎没有动作的长镜头中蔓延开来。
这一场景的声音表现特别有力量,外面风已经停了,只剩下黑暗中的沉默,父亲说着“吃吧”然后咬下生土豆时清脆的“咔嚓”声有着雷霆万钧的效果,预示着生命的底线和死神的降临。
而女儿绝食是故事的情节点III,对土豆的抗拒是对生存的抗拒,因此第五次吃土豆的意义已经被升华至生存与否。
2.《都灵之马》中的风是什么时候停的?
为什么?
在灯灭了的那个晚上停的。
狂风是影片中的摧毁者,(看上去是)问题的根源,它象征着阻碍人们生存的力量。
而随着马的停止干活、绝食、井的干涸、灯的熄灭,在第五天晚上困境已经到达了顶点,再也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可言。
此时击垮人的已经不是物质条件,而是精神状态。
因此起着表征作用的狂风停了,留给人的空白直抵生存问题的根源:父女俩的生存窘境是天生就有了,人类一切悲剧的根源在于“存在”本身。
有了狂风的停止,才有第二天女儿的绝食。
3.《都灵之马》多少镜头?
30个镜头。
第一天第一个镜头:开场驾马-6:00第二个镜头:把马和马车都赶进车棚,收进衣服-11:45第三个镜头:女儿给父亲换衣服,女儿煮土豆和对窗户静坐-17:45第四个镜头:镜头对着父亲吃土豆,吃完后父亲对窗户静坐-23:45第五个镜头:熄灯,洗脸,躺下,“蛀木虫”的谈话1:00:00第六个镜头:女儿出门打水-32:57第七个镜头:女儿给父亲穿衣,父亲喝了两杯酒-37:00第二天第八个镜头:马儿不肯走,拖出来再拖进去-44:22第九个镜头:回到室内,女儿给气急败坏的父亲换衣服-48:14第十个镜头:父亲劈柴,女儿用热水洗衣服,把衣服晾在父亲单手架好的绳子上-51:54第十一个镜头:父亲扎皮带孔,女儿叫父亲吃饭,镜头面对女儿慢慢吃土豆的样子,吃完后女儿收拾盘子,父亲对着窗户静坐-58:15第十二个镜头:一个男人敲门进来打酒,说了一番疯话,扔下两个铜板在风中离开-1:05:35第三天第十三个镜头:女儿起床穿衣,出门打水,风大极了。
艰难地打水回来-1:12:52第十四个镜头:女儿给父亲穿鞋穿衣,父亲起床喝了两杯酒-1:16:37第十五个镜头:父亲走进马厩清理稻草,女儿进来拖走稻草倒到外面,马儿不吃1:19:08首次除片头外首次响起主观音乐-1:20:45第十四个镜头:女儿端出土豆,相机在侧面拍女儿父亲一起吃土豆,吃着吃着父女俩一起看外面,很惊诧-23:20第二次响起主观音乐-23:27第十五个镜头:从玻璃窗前看到远处两匹白马拉着一辆马车朝屋子过来。
父亲让女儿把吉普赛人赶跑。
吉普赛人在井前停下要喝水,被拿着斧头的父亲恐吓到了,离开发癫地说:“我们还会回来的。
水是我们的,地球也是我们的”-1:28:23第十六个镜头:女儿在家里读圣经-1:33:06第四天第十七个镜头:女儿生火,出门打水,发现井里干涸了。
叫父亲过来看。
父女回到家中,父亲喝了两杯白兰地-1:38:18第十八个镜头:女儿收拾马厩,喂马水,马不喝。
-1:40:00第十九个镜头:父亲叫女儿收拾东西,女儿收拾箱子,父亲把东西都搬到中间来-第二十个镜头:女儿把马车牵到门口,父亲把马牵到门口,女儿拉着马车艰难在风中行走-1:52;43第二十一个镜头:父女牵着马车走出树的地平线,然后原路返回了-1:56:10第二十二个镜头:父女一样样把行李搬下车,搬进屋,父亲把马迁回马厩,女儿呆坐在窗前-2:01:56第五天第二十三个镜头:女儿给父亲穿好衣服,父亲起来喝了一杯白兰地,白兰地只剩下一小酌了-2:05:44第二十四个镜头:父亲打开马厩,父女走进马厩,一起凝视着马。
马的特写长达好几秒。
父亲把马嚼子取下。
-2:08:32第二十五个镜头:父亲静坐在窗前看窗外,女儿做针线,之后端出盘子吃土豆,父亲吃了半个就推开盘子重新坐回窗前-2:14:06第二十六个镜头:黑暗突然降临了。
女儿点着了灯,捧着火的样子小心翼翼。
之后坐在墙前盯着灯看-2:17:40第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个镜头:灯的特写,慢慢熄灭了。
女儿重新点燃却点不着,父亲用灰烬点也点不着。
他们上床去睡了。
黑夜里只有他们盖被子和呼吸的声音,除此之外只有沉默。
风不知何时已经停了。
-2:21:20第六天第三十个镜头:父女对坐,没有火了,土豆是生的。
女儿绝食。
4.《都灵之马》为何是黑白片?
《都灵之马》是剖析人类生存问题的哲学电影,不是叙事电影。
现实生活中五彩斑斓的颜色不适合出现在这样宏大而沉重的主题中,也没有必要。
黑白表现的是一种沉重,是一种原始观察,是一种剔除了杂质的思索。
它将现代生活中的戏剧化和多样化抽离,把我们的视界倒退到元谋人时代,看到的是岩洞、寒冬、枯叶和火。
这正是《都灵之马》要探索的生存本源问题,因此黑白让影片有抽离现实的大气美和粗粝感。
黑白是一种二元对立。
影片中有很多对立,父女的黑马和吉普赛人的白马,父亲的黑衣和女儿的白衣,井满和井干,灯亮和灯灭,这些对立的象征用黑白来表现可以直指对立的本质。
黑白是一种隐忍,也是一种挑战。
黑白是收敛的颜色,其实又孕育着所有的色彩。
它符合贝拉·塔尔对人生隐忍的观察,但同时它又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质疑。
黑白两色象征死亡的颜色,是对1889年的尼采致敬。
5.《都灵之马》中,父亲女儿离家后,为何又回来了?
如果寻找现实的线索,父女回来的原因可以这样解释:1.从来买白兰地的男人口中得知,小镇已经被风吹跑了。
父女其实已经无处可去了。
2.马已经丧失劳作力,马车是由女儿艰难地拉着,狂风又如此肆虐,他们根本不可能走得了多久,离开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挣扎。
但其实对哲学思辨意味浓重的《都灵之马》来说,这一幕的象征意义大于解释意义。
1.“生存”于此地是人类的原罪,根本无法逃脱的掉。
地平线是上帝划出的,人类终其一生只能在它的范围内。
2.影片再也没有描述过除了有一棵树的地平线以外的世界,有一个残酷的隐喻:外面的世界不存在。
他们是孤独的,人类是被巨大的孤独和无力感统治着。
(《移魂都市》也表达过同样的思想)3.本片所探索的生存是人类自成一体的灵魂上的东西,是靠自身的感悟而不是求救于外来世界。
哪怕无法得救(其实是必然的),也只能让灵魂在自身内部慢慢萎缩。
10 ) 一个真正让人恐惧的电影
1.这个电影超过了豆瓣的评价系统,五个星星或者再加一个或者再加一个都不够评价这个电影。
2.阿基·考里斯马其说封镜说了很久,结果去年还是拍了个电影;可是贝拉·塔尔既然已经做到这个份上,恐怕他是真的不想拍下去了。
贝拉·塔尔只有五十七岁,去年是五十六岁,作为世界上活着的最重要的几个导演之一,实在是不算老,如果这样就不干了,实在是太扫兴了!
3.就算知道贝拉·塔尔很老,我一直还是觉得他年轻,就像看“金钱”的时候感觉罗伯特·布列松像游戏中转世但是不掉经验值一样,贝拉·塔尔一直像最年轻的导演一样充满最年轻的力量。
有时候总会把他跟洪尚秀或者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这些小他几岁或者十几岁的人联系起来。
4.女主角,就是那个女儿的角色,其实就是”撒旦探戈“里面的小女孩,变化好大;感觉就好像看高峰袖子从”东京合唱“里的小女孩到”女人上楼梯时“里面的女人一样神奇,总会想着一个女人的人生里到底发生了多少复杂而让人费解的故事。
说回“都灵之马”:去年在“都灵之马”之后不久,拉斯·冯·特里尔有个电影叫“忧郁症”,我大概是半年前看的,拉斯·冯·特里尔之前还有一个电影叫“反基督者”,这两个电影都可以跟“都灵之马”联系起来,但是“都灵之马”更恐怖。
主题没什么可说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只能说自己看得见的东西:比如说,长镜头。
在米克洛斯·杨索之后,我没有看过比贝拉·塔尔更好的长镜头了,像“鲸鱼马戏团”那种,又新鲜又有力的东西,让人看了小心肝扑通扑通的。
“都灵之马”也一样,但是收敛了,收到几乎让人可以忘记了,虽然除非必要不分镜,但是只要你稍不留神,就会以为已经是下个镜头了。
正如剪接希望做到剪了好像没剪,贝拉·塔尔做到了没剪好像剪了然后再好像没剪,当然是炫目的技巧,但是他收起来了,而且对他而言,这恐怕不是技巧,而是信仰。
再比如说,沉闷。
没有比贝拉·塔尔更沉闷的导演了,在贝拉·塔尔的电影里没有比“都灵之马”更沉闷的电影了,整个电影不仅沉闷,而且连一个出口都没有,你以为接下来会爆发或者更深的沉闷,但是没有,仔细想想,之前之后都是同样的沉闷。
表个态,我觉得这个很大的优点。
再比如说,开头和结尾。
除掉旁白不说,当然旁白也做得很棒,开头是很厉害的,像贝拉·塔尔之前的开头一样厉害,好像很慢,又好像很快,就像看一个3D武侠片一样,画面很刺激,又好像很闷,在一个镜头里实现了非常多的效果,粗糙并且精致,反正我也说得乱七八糟的,就是很棒就对了。
最后一点,这个震撼的开头有很大的吸引力,把人带入一个几乎什么的没有的电影世界里。
然后是结尾,我想,这是我看过的最让人恐惧的结尾了——当然这种恐惧是靠整个电影完成的,但是在结尾的地方出现效果了。
作为一个认真观看并且投入到剧情和环境里的观众,我所期望的或者恐惧的东西,在结尾通通没有出现,然后就有胸闷和冒冷汗的反应了……我没办法再说下去,说着说着自己就乱了。
我唯一想说的就是,这个电影好到无以复加,如果因为太沉闷——尽管沉闷也是一个优点——就不看,或者看到一半放弃,实在是太扫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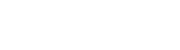




















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幻如一丝尘土随风自由的在狂舞我要握紧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吹啊吹啊 我的骄傲放纵吹啊吹啊 不毁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毁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吹啊吹啊 我赤脚不害怕吹啊吹啊 无所谓扰乱我
很不喜歡這部片子,不是技法上的,而是審美上的。我不覺得我讀到的尼采哲學,是這種和冰冷重複的生活死磕到底誰也不信,最終瘋魔乃至死亡的樣子。如果導演試圖用冗長的鏡頭和頗為無釐頭的神學吐槽來傳達自己對世界的看法,他無疑成功地做到了這點。但我覺得實在有自己更為欣賞的觀測角度。為什麼不能樂觀一點,化腐朽為神奇,化無聊為有趣呢?同樣是困頓之中,王陽明和金聖嘆處理的要棒很多呀。即便是尼采哲學內部,也有巨大而活潑的生命力在。當然,導演主觀未必是要勸諭,很可能只是為了呈現。那就羅布白菜各有所愛,沒什麼好說的了。另,三十個長鏡頭實在太有實驗性了。
Visually striking, it is a pecuilar take on the eternal recurrence and nihilism...
人应该直面自己的局限性,贝拉塔尔就是我的局限性,我欣赏不了……
8.11 中国电影资料馆。9/10 粗粝质感的黑白影像 厚重低沉阴郁绝望的配乐 全方位多视角的长镜序列 循环往复单调乏味的日常 风沙呼啸肆虐永不停歇 世界自光明诞生 又隐入无尽黑暗 于一片混沌之中 重构经典创世神话 是导演对尼采“上帝已死”哲学命题作者性的表达 想起大学时期某次自习时 教室内闯入一位学长 他在讲台上宣讲 为读书协会纳新 并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极力推崇 表示如果没有读过这本书 那我们整个大学生涯将是虚度时光 毫无意义 后来 这位年轻同学被导员请出了教室 联想到电影中父亲和买酒男人的对话 真是奇妙的互文…
很长的大闷片,特别适合在很忙很忙明天有一门考试一个论文死限半夜还要采访这样的日子去看,看完两个半小时抑郁的马和人,你就会意识到:一切都是百忙啊,不如躺下来吃土豆吧。
3.8🌟被上帝诅咒和抛弃的土地,被恒久而暴烈的狂风肆虐和蹂躏的土地,马匹在死去,油灯在熄灭,井水在枯竭,一切生的气息都无法在这片土地上存活下来,吉普赛人可以途径后转身离去,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却像被契约禁锢在此无法离去,只能一点点慢慢死去。
现在看到马铃薯都生理不适想吐……
缺乏对灾难-身体困境的真实感受,于是包装成精神恐吓寓言式的风暴;缺乏对日常生活琐碎苦难的真实体验,于是刻奇为故弄玄虚的慢镜头。马变成了人类自恋自伤的容器,浓浓的人类中心ego,是为一登;拔高爹发呆的思想价值,扁平化女儿琐碎劳动的辛苦,是为二登;2011年已经遗忘大屠杀也尚未面临Covid,于是灾难和绝望只能话语化,变成tag为“尼采爱好者”的身份标榜,现实里还在过着影片里日子的人,绝不会、也不被允许成为这种电影的观众,甚至不如略有镜头暴力的一些纪录片,是为三登。
惯性的平静没有时空对比,你就不应该谈悲苦,你觉得洞穴里的原始人有多少焦虑?美是俯视我的东西,我不自卑也不迎合,只有安睡
感觉浪费了两个半小时。。配乐不错tho
匈牙利#100。想看[2009-09-01]。2011柏林评审团大奖。2016年4月贝拉·塔尔北电大师班大银幕放映过。[2024-03-11]重看数字版。确实是体现中后期(1988以来)贝拉·塔尔美学最完备的一部,末世寓言,世界在七天毁灭(其实也只有六天,毁灭世界也要休息一天么哈哈),通过不断地重复日常制造的差异(尤其是视角上,同时逐步揭示空间)来把不可理解也无可化解的必然死局视觉化,整个影像质感一流(尤其结尾隐入黑暗那段),气氛方面永不停歇的狂风和无尽循环的音乐,实在太厉害了。这片被《一次别离》压一头真是千古奇冤。
还行吧,我不太喜欢压抑的电影
2个半小时,一共30来个镜头,200多句话。反创世和反尼采,似乎是非常固执的平民主义立场。但除了第一个镜头,马都是僵死的啊。镜头的容量似乎也显不足
《都灵之马》将台词缩减至最低限度而产生大量的留白,透过长镜头所不断重复的生活场面来表现生活的枯燥无味的永恒轮回,如同屋外呼啸的寒风:几乎毫无故事情节的发展表象下实际是走向毁灭的过程,马,作为影片的旁观者也类似卡夫卡《饥饿艺术家》的角色而成为尼采的象征。人类亟待被超越。正午前的末日
第六日,井水干涸,油尽灯枯,狂风骤停,女儿静默。父亲啃完最后一个生土豆,等待不会来临的第七日。上帝用六日创造世界,贝拉·塔尔用六幕将秩序重归混沌。精神挣脱之苦与肉体生存之虞,人类的永恒困境,贝拉·塔尔从此种集体命运中汲取养分,完善了电影的最后一种可能性,往后的电影史几乎可以悲观地断言只是对前辈大师的模仿与致敬。“拍完《都灵之马》后,我要说的都已经完结了。”可以一生只看一次《撒旦探戈》,但必须每年都刷一遍《都灵之马》。#2019年7月4K版三刷。
表示亚历山大啊...说了啥?不知道...多一颗星完全是为了对黑白影像的好感
不好,至少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镜头很无聊:穿衣,吃土豆,取水,喂马...六日的生活看得我想睡觉.至于尼采哲学什么的解读还是收收吧,本片我根本没看出对他有什么阐释. 硬套哲学简直是侮辱了电影艺术,难道还想把现代艺术那一套搬到电影里?令人作呕.不过导演水平至少还在,许多地方的处理还是有功底的. 10.9 重看 nc中的nc
不是扯到尼采就有思想的
重复的长镜头+琐碎的日常对话+大段的哲学独白。个人理解,电影想表现的是: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人们内心孤独、虚无、悲观,缺乏饱满的生命意志和崇高的精神信仰,每天重复着枯燥乏味、绝望的生活。